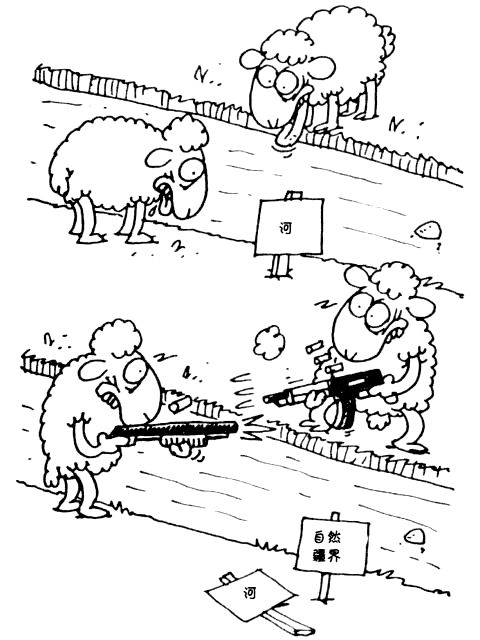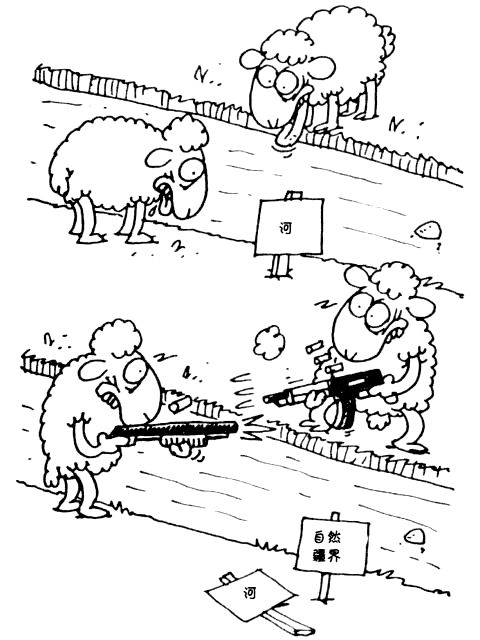“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会‘迫使法国人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吞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族和罗曼语族的各种族的战争’。
“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天天悬在我们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的蹂躏。”
[13] “简言之,所有的公共职位,即使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属于中央政府的职位,也应该由公社的官员来担任,并以此而处于公社的领导之下。若有人说,‘此时我们便无法保证中央的职位是由国家的普遍而整体需求的必然产物,而不是统治人民的职位’,那真是再荒谬不过了。
“实际上,这些职位应当存在,但那些官员本身则不能再如之前处于旧的政府机构时那样自我攫升至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务均应由公社官员来担任,因而处于真正的控制之下。公共职位不应该再作为私有财产而存在了。”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