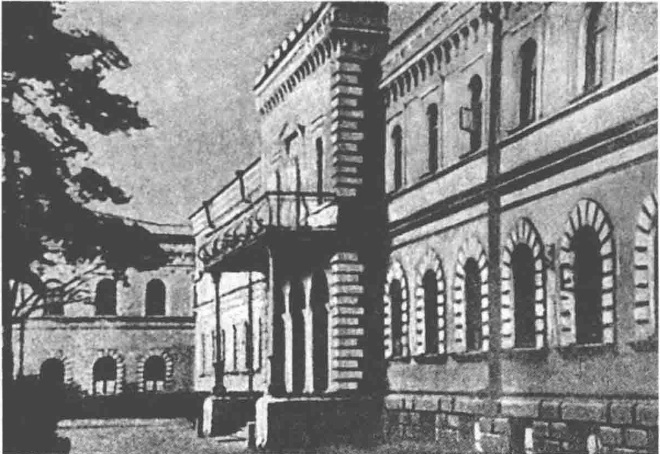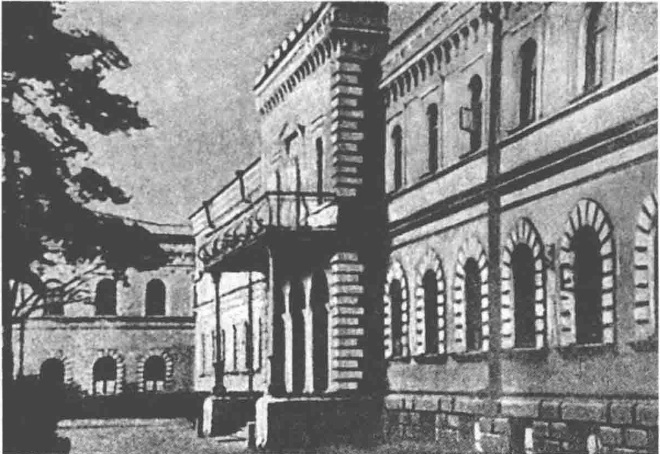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5.楼房里的战斗
中国志愿兵在弗拉季高加索参加八月战斗的情形,直到我们会见了常杨清时,才弄清楚。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消除了大部分的“空白点”。
在第一次会面以前,我们早就知道他了。保存在阿尔玛维尔档案局里的那些内战时期的文件中,有这样一张证明书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常杨清,一八九九年生,中国人。一九一八年志愿参加红军。内战末期,在第三库班骑兵团服务……”之后,是一大张城市和居民点的名单,他曾经参加过保卫它们的战斗。证明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一九三〇年六三日,阿尔玛维尔城红色游击队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常杨清·尼古拉为红色游击队员,并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四日发给他第十二号证明书。”
提起第三库班骑兵团来,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一支很出名的团队。从这张证明书中可以得出结论,原来骑兵团里也有中国战士。不管怎么说,总有一个,他叫常杨清。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我们找了好长时间,最后才打听到,常杨清在切禅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一个集体农庄里当栽种水稻的指导员。
我们就在收割后的、光秃秃的稻田里第一次会晤了。我们把一抱稻草垫在身子底下,在地上坐着,紧靠着这位须发斑白、满脸皱纹,但眼睛却奕奕有神的老人,倾听着他不慌不忙地讲述自己那些动人的故事。
常杨清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生活。一九一六年,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时,就离开了中国。像当时成千成万的其他中国劳工一样,他来到遥远的俄国找工作。起初,他在乌拉尔工作,后来在蒂拉斯波尔和敖德萨。就在那儿遇到了革命。
“一九一七年,”常杨清回忆道,“敖德萨有很多中国人。有的在码头上做装卸工人,有的干粗活儿,有的在采石场砸石头。
“起初,我们还不大理解震动了整个俄国的那些事件,后来就理解了,因为后来出现了中文的传单,还来了许多宣传员。
“有一个姓张的对这类问题解释得特别好。他是河北人。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俄国话说得呱呱叫,比我在俄国住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要讲得好。这是因为他从小就在俄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里上过学的缘故。
“我知道传教士教给老张的是些什么。他们教给老张,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人类、动物、植物。它还创造了现有的一套秩序。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合理的。世界上有富人,这是合理的;世界上有穷人,也是合理的;那些官吏、厂主和地主老爷们统治着人民,这是合理的;要人民千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这也是合理的。要是人民觉得生活太苦,这就更好,因为谁在这个世界上受尽了苦,死后一定能上天堂……
“不单是那些俄国神父这样欺骗他们,佛教的和尚也是这样传教的。常言说:谁喂养金丝雀,金丝雀就为谁歌唱。这班神父、牧师是靠谁养活的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传教士们想把老张栽培成自己的助手,让他在中国人民当中传教。可是事情恰恰相反,老张来到俄国,呼吸了革命的空气之后,却对中国劳工们传播了另一种道理。”
“‘布尔什维克是卫护人民的,’老张说,‘他们希望政权能转到人民手中。他们不在人与人之间划分等级:俄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他们认为全都一样……’
“我们越来越对周围的事情产生兴趣了。我们把那些拥护沙皇、财主和旧秩序的人叫做立宪民主党人;把那些卫护人民,拥护革命的人叫做苏维埃人。
“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更替了二月革命时,我们高兴极了——人民占了上风。当我们看到,敌人怎样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人民政权时,我们明白,必须挺身来捍卫它。我当时想:如果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胜利了,世界各族人民就会过得好一些,如果失败了,那么大家就会过得更苦。
“一九一七年十三月﹝原文如此,待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我参加了赤卫队,拿起武器,决心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有很多。人们把我们集合到一起,编成了一个中国连。从河北来的老张当了连长,就是一开头就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那个老张。
“一九一八年春天,当敖德萨开始疏散的时候,捷克士兵、塞尔维亚士兵和中国士兵被合编成一个部队,接受护送国家银行库存黄金的任务。黄金很多。你们知道轮船的船舱吗?一箱箱的黄金把整个船舱都塞得满满的。这是一种非常麻烦的货物……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一听到有黄金,马上就会发疯。在轮船上出了多少乱子哟。不是打枪,就是闹事。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接到多少金子,就运走多少金子。全数运到。”
常杨清记不清这支国际部队队长的名字了。他说:“他好像是捷克人,不过也可能是塞尔维亚人,当时我分不太清……”我们觉得这位队长不是中国人,所以没有详细追问他。
不久,命运突然使我们和这位队长相遇了。一九五七年夏天,我们在编写《世界劳动人民的事业》这本集子时,认识了许多如今还健在的、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的国际主义者。其中有一位叫阿多里弗·席别克,这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是红军中那些捷克分队的最初组织者之一。原来他就是常杨清回忆到的那个国际部队的队长。
“当时运送的黄金很多。”阿多里弗·斯杰潘诺维奇·席别克向我们讲道,“当我们在费奥多西雅下船时,需要整整一列车才装得下这些金子。护送列车的是中国士兵。中国士兵在纵队里有两百来名,由一位姓张的同志指挥。这是一个勇敢而坚定的人。我完全可以信赖他。当然,我也信赖所有的中国士兵。有时候,我简直被他们的坚韧不拔、遵守纪律、沉着冷静,特别是他们那种高度的、仿佛是与生俱来的革命自觉性深深地感动了。在护送‘黄金列车’这段漫长的、艰辛的路途中,遇到许多危险,打过几次小仗,和敌人进行了多次的交锋,在两百来名中国士兵中,没有一个人做过任何违背自己职责的事。这是一些极其忠诚的人!”
当然,阿多里弗·席别克记不得中国连里的列兵常杨清了。当我们把这位中国老战土的一张近照拿给他看时,他还是记不起他来。
可是,席别克本人却比较容易被人认出。他有一张四十年前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年轻,直挺挺地站着,穿着军服。我们和常杨清相遇时,就把这张照片拿给他看,他马上就从照片上认出这是过去的敖德萨国际部队的队长。“他非常勇敢,”常杨清这么称赞他,“什么都不怕。一天到晚忙来忙去。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过觉。”
国际部队队员把这列满载黄金的列车护送到尔蒂谢沃城。在这儿,阿·席别克把这批贵重物品移交给以党中央委员会全权代表密德维杰夫为首的委员会。后来,这支国际部队就分散了。阿·席别克记得,中国连开拔到南方去了。
由于常杨清的帮助,我们弄清了这个不够明确的“南方”。中国连离开了尔蒂谢沃城以后,在老张的指挥下,转战于库班附近的吉马谢夫、齐霍列茨克、拉宾斯克和涅文诺麦斯克一带。在频繁的战斗中,这个连队损失了大部分成员。老张也牺牲了。于是,常杨清就领着剩下的一些士兵来到了弗拉季高加索,加入了包清山领导的中国营。他在那儿参加了八月的战斗。后来又和弗拉季高加索的这一部分队伍开赴阿斯特拉罕。
我们在常杨清这间清洁整齐、幽雅宜人的屋子里度过了几个晚上。看来,我们要问的都问过了,他要讲的也全讲了。可就是舍不得和他分手。这段不寻常的、回忆起来仍十分清晰的往事使他非常激动。毫无疑问,他还知道许多东西。
于是,我们就动员常杨清和我们一块儿到奧尔忠尼启则去。我们想:“也许,旧地重游,他还会回忆起一些东西来。”
事情正是这样。我们来到了这里,陪着这位老战士重访了他早就熟悉了的故地。许多情景又在他的记忆里重现了。
我们先去看了曾经矗立着里涅依教堂的那个地方。这个教堂现在已经没有了。中国战士曾经在那儿进行过保卫战的那座钟楼也没有了。尽管这样,常杨清仍然记得如火如茶的一九一八年八月在这儿所发生的一切。那时,虽然他自己在库尔斯克郊外作战,但他的伙伴们,也就是在钟楼上作战的那些英雄们,对他讲述了全部经过。
“他们一共是三个人。当时,连长苏老九认为必须占领钟楼,因为他明白:谁占领了钟楼,谁就能控制整个区域。他给他们发了一挺机枪、许多子弹、几袋面包和几壶水,命令他们三人爬上钟楼,对他们说:‘你们好好监视着,别让一个白匪从任何一条街上越过。看准了再开枪,别白白浪费子弹。如果情况允许,你们就休息;情况不允许,你们就坚持到底!’
“苏老九交代的这些任务,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对白匪进行了十天十夜的射击。”
这样,由于老战士常杨清的帮助,我们知道了:在里涅依钟楼上坚持战斗的三个英雄的名字是:
王德盛,郭一鲁,季凤乔。
我们还了解了在离里涅依教堂不远的一座又长又阴暗的军事机关大楼里所发生的几次残酷的战斗。当时,红军部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这座大楼里。
在这里曾进行过楼层战,战斗是上下垂直对打的:白匪占领了一层楼,二十来个中国红军战士则坚守在二层楼上。
白匪起先不知道他们是在和谁打交道,他们一面往上射击,一面喊:“投降吧,布尔什维克们;我们不触犯俄国人,也不触犯沃舍梯人,不过,如果你们之中有中国人,那你们就得吊死他们。我们一块来吊死他们。”
楼上响起了一阵阵的步枪齐射声作为回答。
但是,步枪的射击不论是对于占领楼下的人或者是占领楼上的人,都没有什么大的伤害。这座建筑了,上百年的楼房的墙,只有用要塞炮才打得穿。这场战斗要分个高低,不光是使用武力,还得使用计谋。第一种办法对我们的战士来说是不行的:力量的对比对他们显然不利,于是就只好使用第二种办法了。
起初,白匪听到头上有敲击声,以为有人想打穿天花板。他们细细地倾听着:红军在耍什么花招呀?难道他们想打个口子跳下来?
指挥哥萨克白匪的一个上尉,把他的人都布置好,叫他们做好准备。
可是,当天花板被打穿了拳头那么大的一个窟窿时,红军却安静下来,不声不响了。白匪这时却忙起来了。他们朝天花板上那个打穿了的小窟窿一个劲地射击,直到白匪上尉命令他们停止为止。这不是非常明白吗?从这种角度来射击,根本伤不着楼上的任何人。
白匪没有一点办法,只是气得破口大骂。毫无疑问,这些不堪入耳的“脏话”不能不传到对方的耳朵里。
白匪本来以为会听到楼上的回骂,但却没有。可是,在那个打穿了的窟窿中却出现了一张用绳子拴着的纸条。红军不慌不忙地往下放着这张纸,停停放放,放放停停。当纸条放到伸手拿得着的时候,一个哥萨克白匪就过去解下纸条,展开来看。
纸上画着一幅铅笔画:一个细眼睛的、满面笑容的中国红军战士,帽子上缀着一颗红星,将拇指插在食指和中指间,给一个戴着肩章、脑门上留着一绺长发的大胡子哥萨克白匪看,以此来侮辱他。
白匪都围拢来看这张画。看来,这正是楼上的人所期望的。从天花板上的小窟窿里飞下来了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楼下的白匪幸存的没有几个。
后来,红军战士又把楼上其他几个房间的天花板也打穿了。就这样,包清山的士兵们没打一枪就压住了敌人。
他们还利用了“钟摆式”手榴弹。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中国红军战士惊人的智慧和善于利用“楼层战”的特殊条件。
“钟摆式”手榴弹是这样投掷的:把手榴弹拴在绳子上,从窗子里甩出去,甩时要这样计算好:必须让手榴弹像钟摆一样在空中来一个弧形的摆动,摆回来时正好飞进一楼的窗口去。
这产生了不小的效果。白匪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感到心惊胆战,惶惶不安,并且也遭到了不小的损失。
他们却不能照样回击中国红军战士们:他们在楼下,无法把手榴弹从天花板上的小窟窿里投到二楼上去;同样也不能用“钟摆式”手榴弹去击中楼上的目标。
诚然,白匪利用他们在一楼的优越性:关闭了水龙头,切断了二楼的水源。
中国战士的处境非常困难,那时又是八月,正是夏日炎炎的季节。
白匪已经在庆贺胜利了。红军还能跑到哪儿去哟!他们口干舌燥地待上一两天之后,就是空手也能把他们抓住。
但是,敌人却没有估计到中国战士那无穷无尽的智慧。
被包围的包清山的战士们所在的那个院子周围,有一道高高的砖墙,砖墙的一头紧挨着一所中学的场院,从那儿可以潜入库尔斯虎镇。从那日日夜夜传来的射击声中,不难猜出,镇子还在坚持、那儿有自己人。
可是,怎样爬过这道围墙呢?
红军战士仍旧利用手榴弹。他们储备的手榴弹非常充足。夜里,当楼与楼之间的激战沉寂下来的时候,一位中国战士悄悄地爬过院子,把一捆手榴弹放在围墙下,在爆炸管的环上拴上了一根捻子,然后又往前爬了一段路,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
战士们得到了他的信号,就把剩下来的手榴弹从天花板的窟窿投到楼下的空屋子里。白匪开始骚动起来。当白匪在屋子里东奔西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中国战士的整个小组却从二楼的窗子爬到楼下的院子里,并朝围墙上炸开了的一个大缺口冲去。
这座四十年前进行过楼层战的军事机关大楼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如今,它仍然像一座牢不可破的纪念碑似的,巍然耸立在市中心。
过去属于什杰因盖尔男爵并曾做过捷列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办公处的那座大楼已经不存在了。不然,它也可以作为曾经在八月的英勇战斗中洒过鲜血的、坚毅勇敢的中国红军战士的纪念碑。
包清山的这几个战士在这里坚守了五天五夜。当他们的子弹打完了,他们就用刺刀和枪托还击敌人。最后,小组只剩下了三个人。他们的力量已经全部消耗完了。而白匪军此时却以十个人来猛击他们每一个人,因而战胜了他们。敌人开始残暴地折磨他们,拴住他们的两只手,把他们吊在树上,在三位英雄的背上刻上五角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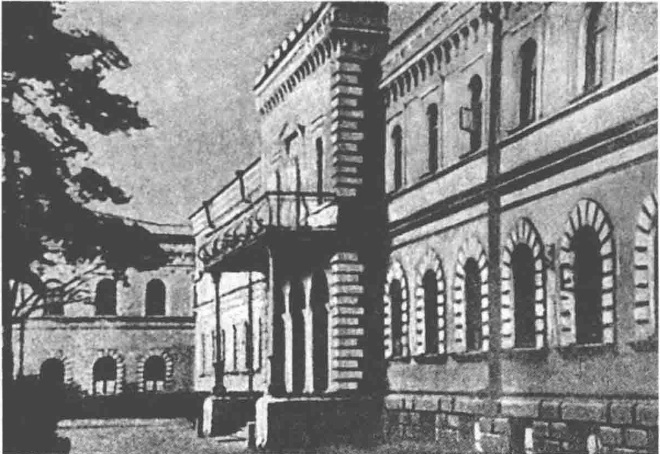
奥尔忠尼启则市中国营战士与白匪军进行战斗的楼房
什杰因盖尔大楼很快就被红军打下来了。但是,三个红军战士中有两个已经牺牲了。
当人们把那个奄奄一息的中国战士从树上放下来,并使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枪在哪儿?把枪给我!……”
他四肢无力,但却立刻投入了战斗。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