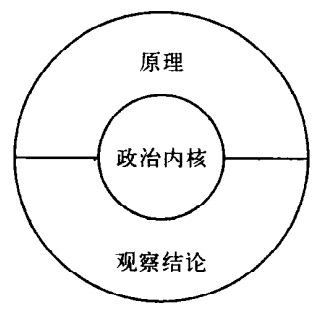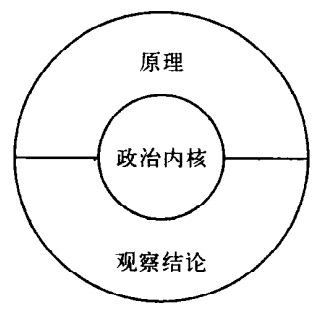逻辑一致性(部分的和总体的)也许存在,也许还将继续被忽视,或因为种种理由得不到响应,因为一个人头脑中的所谓相互矛盾,也是这种情况。只不过通过在不同的情境下到处转化这些矛盾,通过对例外、包容和排斥形成特殊的、有时是更普遍的标准,并通过用避免认知困难的种种方式对一种情况的定义提出令人惊异的足智多谋的伦理诡辩,有许多矛盾的个人能活得相当好。只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时间和环境通常的安全舱口已被封闭,个人被迫去应付他的种种矛盾。把握科学理论也同样;我们已经学会与科学理论的矛盾共存,这些矛盾部分已经通过解释消除,或者也许还将继续被忽视,或大多数时候不受关注。仅仅是在例外的情况下,这些矛盾才变得相互关联,而且差异也彼此相关……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