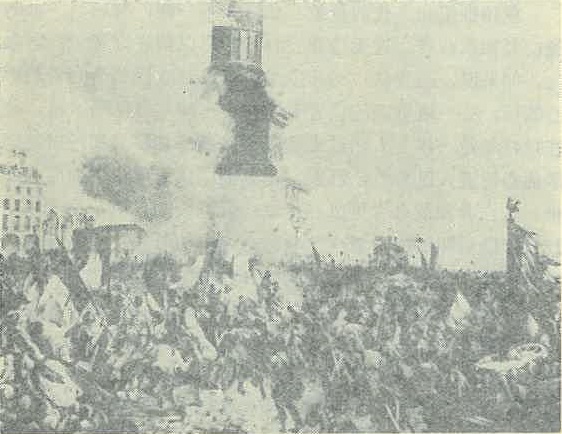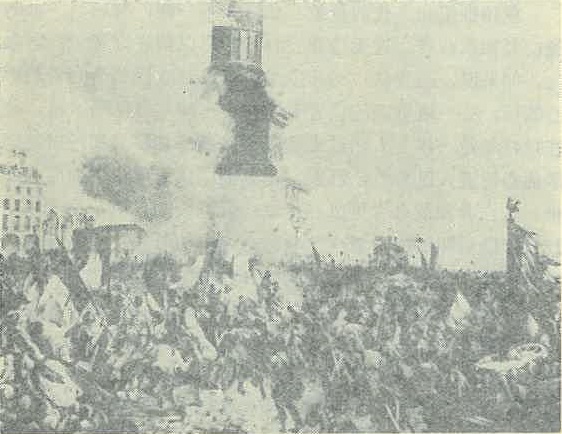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阿萨·勃里格斯《马克思在伦敦》(1982)
3 流亡者与革命者
在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如同巴黎一样,有相当一批的流亡者和革命者,这无论在1848年革命以前或以后都是如此。如果说,巴黎从1789年以来被看成是欧洲革命的天然中心的话,——用俄国流亡者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话来说,他在1847年是“怀着人们过去朝觐耶路撒冷和罗马那种肃然起敬的心情进入巴黎”,那么,伦敦便以成为避难所而闻名于世。流亡者和革命者可以在伦敦获得更大的自由,这无论在1851年以后即法国重新成为拿破仑帝国的时候,或是在1848年革命前夕即路易·菲力浦仍然在位的时候,都是如此。
甚至在这两段时间前后,当法国革命出现那么多的波折以及它对流亡者和革命者的态度如此变幻莫测的时候,人们更是珍视侨居伦敦的那种安全。的确,在1834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埃蒂耶纳·卡贝就曾利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作为基地来创作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第三个大城市——布鲁塞尔,虽然兼有伦敦和巴黎的若干长处,但从来没有成为流亡者和革命者的久居之地。瑞士也是如此,尽管这个国家直到20世纪还对革命流亡者保持着吸引力。
普鲁士驻伦敦大使本生男爵,在1851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当时伦敦有一千名属于不同政治社团的外国难民。外国政治难民的数目从1849年即马克思搬到伦敦的那年起便有所增长。然而,在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早在1846年,即该协会的组织人卡尔·沙佩尔写信向马克思报告协会活动的时候,已经有250名会员。这些德国人集中在马克思后来所熟悉的伦敦那些地段,在德鲁里巷租了一个大厅进行活动。然而沙佩尔在报告中兴奋地指出协会“正在设法进入白教堂区(又译怀特柴泊),那里有好几千德国人”。该协会终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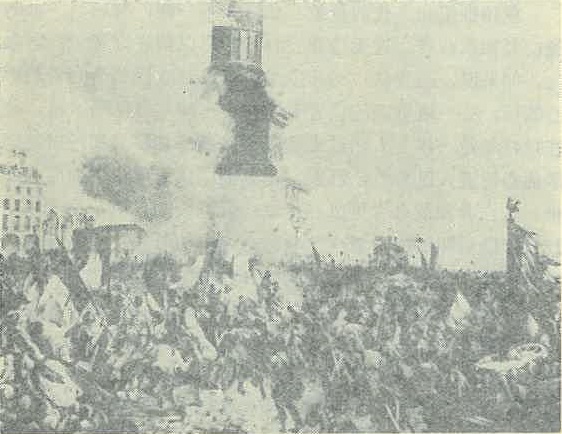
1848年巴黎革命起义。
暴动群众在巴士底狱广场焚毁路易·菲力浦国王的宝座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于1840年在大风磨街(见第46页地图)成立,这个地方在索荷边上,离皮加迪利广场不远。该协会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据沙佩尔说,它到1847年已经吸收了40名斯堪的纳维亚人和20名匈牙利人,“此外,还有波兰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瑞士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以及英国人等等”。
广义地说,在伦敦的流亡者和革命者当中有着各种不同民族的团体,尽管这些团体的旗帜鲜明程度和组织严密程度有所不同,然而它们当中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却很活跃和流行,这在民族受到压迫的波兰人和国家尚未统一的意大利人当中,尤其明显。沙佩尔把一些意大利人开除出去,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确实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朱泽塔·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运动是自由主义的,这个运动依靠——虽然不是完全地——中产阶级的强有力的支持。
尽管如此,不同民族的要求和全人类的要求还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当时总是有许多国际性活动(不单纯在民族节日举行)。此外,由于人们往往正确地看到,流亡者所反对的秩序,其势力是超越国界而勾结在一起的(其中如哈布斯堡帝国,它既是多民族又是反民族的国家)。有鉴于此,团结一致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乃是流亡者和革命者的义务。这无论在1848年革命起义之前还是在1849年以后欧洲的反革命势力得到巩固的时期,都是如此。而俄国军队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加剧了人们对俄罗斯帝国的敌视,以至连从沙俄专制制度下逃出来的俄国流亡者和革命者,也都成为流亡者和革命者当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伙。
相形之下,波兰人从一开始就在宣传和组织上崭露头角,从而受到英国宪章派人士特别是乔治·朱利安·哈尼的热烈欢迎。哈尼曾于1843年在里兹的宪章派《北极星报》报社(该报在伦敦的社址在大风磨街)会见了恩格斯并约他撰写两篇有关欧洲社会主义的大块文章。
另一名宪章派人士威廉·洛维特,是伦敦工人协会的创始人之一,鼓吹一种独特的“道德力量”。他跟哈尼一样具有国际主义观点并于1844年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性社团——世界民主友人协会。他跟朱泽培·马志尼成为密友,在当年年初英国政府扣截马志尼的信件后,他对马志尼进行强有力的声援。但是,他的这个新成立的协会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就,原因是它缺乏战斗性,对大多数流亡者没有号召力。而比较成功的是由哈尼建立的民主派兄弟协会,这个协会是1845年9月在一次为庆祝法国1792年共和宪法而举行的宴会上宣告成立的,其会员包括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民主协会)、瑞士人、匈牙利人以及一名“土耳其民主人士”,他在这个成立宴会上向到会来宾演唱了土耳其的歌曲。
但是,并不是所有在伦敦的流亡者和革命者都对哈尼的左翼宪章运动表示肯定。的确,在流亡者和革命者之间,社会分歧往往比他们当时和以后的民族分歧更显得重要。在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以后,在伦敦的波兰人当中出现了深刻的分歧。然而,德国人的社团则趋向左转,特别是在1847年至1849年间,他们已经对马克思抱欢迎的态度。从职业来看,他们多半是手工业者。沙佩尔是排字工人,莫尔是钟表匠,鲍威尔是鞋匠。第四名积极分子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是个裁缝,他后来在跟马克思的交往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卡尔·沙佩尔任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德国书记。他在来到伦敦以前曾流亡巴黎,并且跟约瑟夫·莫尔和亨利希·鲍威尔一样,参加过那次流产了的巴黎1839年起义。他们都是一个秘密团体,即在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当时都已经是饱经风霜的“职业革命家”。例如,沙佩尔早在1833年就曾经参加袭击法兰克福的警卫室,并且参加过马志尼在1836年发动的那次以失败告终的萨窝依远征。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对正义者同盟的活动起了掩护作用,然而它本身也进行了生气勃勃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它有一个分支机构——星期日俱乐部。该俱乐部甚至吸引了一些不同政治的人。沙佩尔在1846年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不仅概括地谈到协会开展工作的方法,而且还涉及它的思想作风。他写道:
“我们的协会大约有250名成员,我们一个星期集会三次,有关当前政治的报告和讨论放在星期二交叉进行。其中一个星期二用来学习费尔巴哈的《未来的宗教》,我们逐段进行讨论;接着一个星期二用来研究协会会员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们最近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共产主义国家中青年的培养。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给全体成员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把还不明白的有关我们原则的问题提出来讨论,以求全部弄清楚。星期六晚上用来唱歌、欣赏音乐、朗诵和阅读有意思的报刊文章。星期日有各种讲座,包括古代史、现代史、地理、天文等等,然后讨论工人阶级的现状及其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等问题……星期一法国协会进行活动,在那里讨论共产主义制度问题。的确,这个协会看起来仍然很像共和主义组织,不过我们还是从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并且有机会让法国人了解我们的思想。
我们每两周跟英国人(“民主派兄弟协会”)聚会一次,我可以说这种聚会对于双方来说都很有好处……
星期三晚上有歌咏课,星期四有语文和图画课,星期五有舞蹈课。我们图书馆大约有500本书。此外,我们有地球仪和天文仪,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报纸。我们跟法国、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匈牙利、德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保持很好的联系。在这些国家里有我们协会的老会员,他们不时把本国的运动取得的成就报告给我们。”
沙佩尔这封信是寄给当时作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组织者马克思的。该委员会于1845年设在布鲁塞尔,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流亡到那里。他们两人当时已经得出马克思在1845年明确阐明了的结论(在他写的关于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们还在1845年夏天一道去访问英国,恩格斯把马克思带到曼彻斯特,不仅让他看到这个欧洲的主要工业城市的面貌,而且还让他见识了有大量英国经济学家藏书的著名的切特汉姆图书馆。
要考察马克思在1849年到伦敦定居之前和此后他跟伦敦流亡者和革命者团体之间的联系方式,就有必要事先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他是怎样到布鲁塞尔的?他跟巴黎的联系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要求助于英国经济学家去了解社会的本质和革命的前景?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