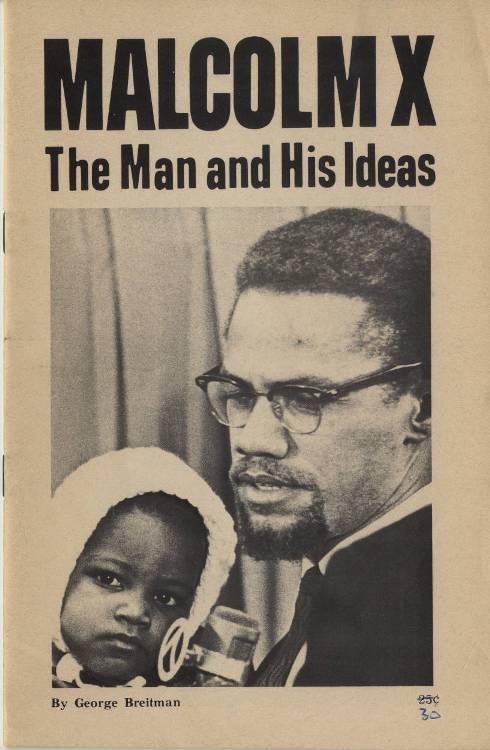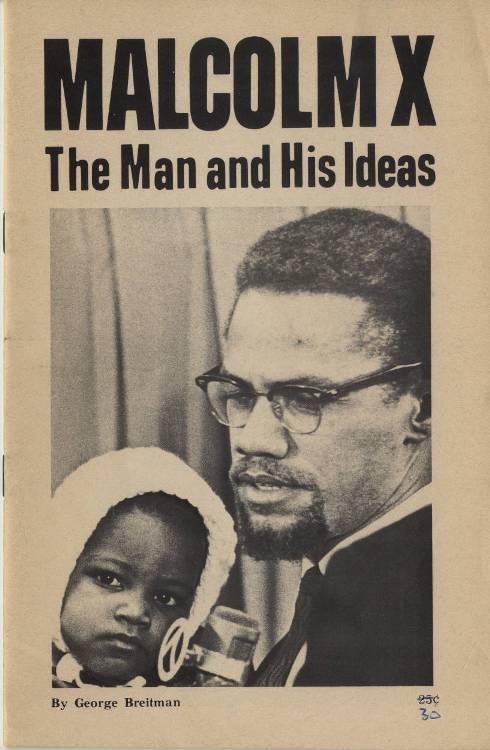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Malcom X: The Man and His Ideas
马尔科姆·X:其人,其思想
﹝美国﹞乔治·布莱特曼(George Breitman)
1965年
杨云舟 译、谷书存 校对
本文为乔治·布莱特曼于底特律“尤金·维克多·德布斯”礼堂(Eugene V. Debs Hall)向“周五晚社会主义者论坛”( Friday Night Socialist Forum)所作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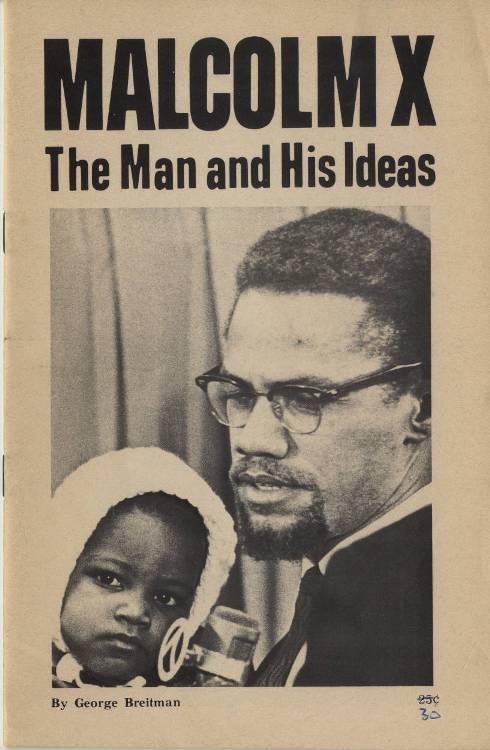
现在要提起马尔科姆·X的罹难依然令人痛苦万分。当下若想全面地对其予以评价恐还为时尚早,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公正、全面地衡量他。马尔科姆的死之所以如此怆痛,是因为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里,我们倏间变得更加渺小、无力,更加脆弱。
我们怅然若失,不仅为他的家人,也为他本建立着的运动,还为黑人群体,更为整个革命事业。每个人心中都有恸哭的冲动,因为不忍面对他仍值壮年却死于非命的事实;因为马尔科姆依然年轻,还没来得及为这场斗争、为人类的解放贡献出他全部的、所有能够献出的力量。
二十五年前,当另一位革命家遇刺身亡时,我还是个青年人,而那位革命家名叫列夫·托洛茨基。当时的我或许并未完全意识到托洛茨基在领导、洞见和政治智慧上的重要程度,又或受到了广大同辈的影响,认为情感宣泄是懦弱的表现。总之,在托洛茨基殒命后,我没有哭。但马尔科姆离世时,我却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我并非认为他在此二人中更为出众。我为马尔科姆哭泣原因之一是,三十九岁的他还处在人生的上坡路,正在为他的抱负奋斗,由他领导的运动也方才起步;而六十岁的托洛茨基则早已迈入了思想和事业的成熟期,业已为今后的运动打下了牢固的根基。不管是战争、迫害——来自轴心国,也来自同盟国——冷战行为还是政治猎巫都无法抹去他的贡献。
但即便谈论马尔科姆仍是如此令人痛心,想要全面评价其人也尚还困难,我们至少能着手审视他的思想遗产及其形成经过。于此,我们要尽力从情绪中抽离,加以克制。这便是三周前,马尔科姆在底特律讲演时所提倡的精神——清醒地思考当前的斗争,思考权力结构扼杀、阻挠斗争的方式;清醒思考,依仗理性,拨云见日。
家庭背景
在西印度群岛被一名白人男性奸污后,马尔科姆·利特尔的外祖母诞下了他的母亲。马尔科姆四岁时,他一家的居所遭三K党徒付之一炬。六岁时,其父不幸惨死,据信是因私刑遇害。
马尔科姆的家庭自此支离破碎,年轻的他开始往返于福利院和寄宿家庭之间。他曾就读密歇根州梅森县的一所小学,成绩优异,却在十五岁的年纪戛然辍学。马尔科姆接着去到波士顿投靠姐姐,打工维生。在当时,像他这样的黑人小孩只能去擦皮鞋、卖汽水、在饭店打杂、在开往纽约的列车餐车上帮手、或者在哈林区的食肆里侍客。不久,马尔科姆便于波士顿地下世界的堕落中沉沦。他开始赌博吸毒,偷拐抢骗。这些都记载在他即将出版的自传里,包括是如何因入室行窃被捕、定罪并被判处了十年监禁。这是1946年的事,马尔科姆才不到二十一岁,和在座的许多听众年纪相仿。
丛林法则
马尔科姆彼时怀着的是怎样的信念?那时的生活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片丛林,只有最凶悍的人才能生存——抽刀杀向弱者,人人各为其主,皆受丛林法则的驱使。马尔科姆的第一份工作是拜一位朋友所赐。那位朋友向他忠告:“一定记住,这世上所有东西都是拼出来的。”
马尔科姆的父亲生前一直仰慕马库斯·加维,但“种族自豪”对还身穿“阻特装”的小马尔科姆来说简直天方夜谭。他东施效颦地试图把一头非洲卷发拉直成白人的模样。他的见识都从白人那里得来,也正是白人将种族社会的伪学装进了他的脑子。在今天的黑人区,太多的年轻人和1946年的马尔科姆别无二致。
狱中皈依
监狱有如地狱,但亦是用来思考的好地方,许多重要的抉择都诞生在监狱。我们所在的这座礼堂得名于尤金·V·德布斯,他正是于1895年下狱时皈依了社会主义。同样在狱中改信的马尔科姆即将迎来人生的转折。
通过家书往来和亲友探视,马尔科姆得知了一个由伊利亚·穆罕默德率领、名为“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的组织。此美国教派在民间俗称“黑人穆斯林”,视安拉为真神,奉行正统穆斯林的部分礼法,某些地方稍作更调,尤其是种族相关的内容。
伊斯兰民族教诲道,当人间还是乐园时,最初的人都是黑皮肤。白人是堕落而低贱的亚种,命中注定在统治世界六千年后灭亡。六千年之期现已终结。黑人能够在即将来临的灭世之灾中幸免,但唯有与白人彻底分离、并信奉安拉的信使——穆罕默德——方可得救。
站在科学的角度,“黑人穆斯林”不过是和其它宗教一般玄妙的神话传说。但在宗教团体外,“黑人穆斯林”亦是一场潮流运动。它的存在为底层社会提供了庇护和希望,为自我革新带来了激励。在一个残忍、压迫的世界里,它将手足同心、团结一致的精神传播了开来。
有关“黑人穆斯林”运动的细节,我在此不加赘述,有数目可观的文献供大家参考。我想指出的要点是,马尔科姆在狱中彻底皈依了宗教,奉伊利亚·穆罕默德为圣人,相信伊斯兰民族能将他和他的族人领上一条通往救赎之路。
自我教化
马尔科姆上到八年级就辍学了。在服刑的日子里,为了能在出狱后更好地参与“黑人穆斯林”运动,他开始自学演讲与辩论。不知从何学起的他只好先翻开字典,把认为有用的单词誊抄在一张表格里。但才翻完字母A打头的词,表格就抄不下了,词语之多让马尔科姆惊讶不已。他从A一直翻到了Z,并感悟到:“有生以来头一次,我能真正看懂一本书上都写了什么。”马尔科姆的经历可谓是密歇根州——乃至整个美国——黑人受教育程度的缩影。
从那时起到他出狱,马尔科姆只要有空便一头扎进图书馆,按他的话说“去挑上几本书读”。不消数年,他将跻身美国最伟大辩论家的行列。政客、大学教授、记者和任何敢于挑战他的人,无论黑白,都不在话下。
在黑白两色的贫民区内,隐匿着不可计数的天赋才智。只需赋予其生活的希望和目标,他们便能挣脱束缚,发光发热。
组织才能
六年铁窗生涯后,在1952年的春天,二十七岁的马尔科姆从长兄威尔弗雷德那里得到了一份工作,也因此被批准假释。出狱后的马尔科姆在底特律的贫民区干起了家具销售。同年晚些时候,他赶赴芝加哥听伊利亚·穆罕默德演讲,二人初逢。伊斯兰民族运动吸纳了马尔科姆,并赐名“马尔科姆·X”。他自愿承办起底特律方面的组织活动,成绩斐然。底特律清真寺注册的信众数量翻了三番,马尔科姆也被提拔为了助理传教士。
1953年底,马尔科姆迁往芝加哥与穆罕默德共同起居,接受了数月之久的训练。穆罕默德把他派往了尚还没有任何清真寺的费城。不到三个月,一座清真寺拔地而起。马尔科姆显然有着非凡的才干、精力和投入。穆罕默德钦点他去领导纽约方面的运动,于是在1954年,不到30岁的马尔科姆重返纽约哈林区。不出数年,他便助偏隅一方的“黑人穆斯林”名满美国,他自己也蹿升为全美名人,成为了趋之若鹜的演说家和激进青年的偶像。
演说家马尔科姆
在顺着时间继续讲起之前,我想特别提一下马尔科姆的演说才能。我本人并非专长于演说,如果有专家能就此作一番研究便再好不过。现存材料不少,马尔科姆的许多言谈都有录音留存。
他的演说风格独特。扼要,干练,如同箭矢,不加丝毫矫饰。他修辞求简,扎根于广大听众的寻常经验。马尔科姆深谙大众心理,了解他们所感所想和强弱之处。不费一句多余口舌,也不加半点阿谀奉承,便能直击听众的理智与情感。不过,虽然有着超凡地打动、激励之能力,马尔科姆的首要武器依然是理性而非感性。
尚在早年间,还在谈日后将遭摒弃的思想时,马尔科姆就已经如此。比如他63年十一月在底特律群众大会(Grass Roots Conference)上为黑人穆斯林所作之演讲,资料能从非裔美国人广播录音(Afro-American Broadcasting and Recording)出版社找到。这是马尔科姆一生所作最伟大的演讲之一。尽管并未反映他的后期思想,但依然值得反复细听,因为刚才所提到的品质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有许多媒体诽称他为“煽动家”。但从这份演讲中我们能听出,马尔科姆与所谓的煽动家截然不同。他的力量完全来自于理性。
这种风格亦迥异于伊利亚·穆罕默德。首先,穆罕默德并不具备马尔科姆的幽默和机智。更关键的是,穆罕默德演说的力量来自于宗教,来自于神圣权威与身后来世;马尔科姆的武器是理性,是逻辑。马尔科姆关注的是现实和当下,即便仍出入穆罕默德左右时也一样。穆罕默德的讲道只有虔诚的信徒才听得进去,但马尔科姆的成功不只限于穆斯林群体。
寥寥数语不足以完整的勾勒出马尔科姆的演说生涯。我只希望抛砖引玉,把更深入研究的机会留给更有能力的人。我唯一要表达的是,在向最受压迫群体进行思想传递这方面,美国历史上再鲜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不仅仅是技巧问题;技巧是通用的,任何人凭借都能学习掌握。马尔科姆可贵在于能与受苦之人有如此紧密的联结,能如此成功地与他们沟通;因为他为他们发声,他视自己为他们中一份子。马尔科姆是受压迫者对自由之渴望的真切表达,是来自受压迫历史的产物,正如列宁是俄罗斯人民的产物一般。
分道扬镳
我们现在来到了1963年,马尔科姆第二个人生阶段的终点。在接下来的1964年三月,他将与穆罕默德分道扬镳。1963年是黑人运动风起云涌之年,千千万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在这一年,黑人运动从南方发展到了北方城市的贫民区,那里也是“黑人穆斯林”的堡垒。民权运动尚未演变为革命,但俨然是革命的序曲。这一背景诞生了一个困境,最终引发了“黑人穆斯林”运动的危机。
“黑人穆斯林”的激进立场促进了其它黑人组织的左倾,这是积极意义。但当斗争真正到来时,“黑人穆斯林”却往往隔岸观火。他们言辞激烈,但对非穆斯林黑人的遭遇却袖手旁观。白人和黑人造反派两者与他们皆非同路。
在“黑人穆斯林”内部,分歧初现端倪。受马尔科姆影响、更加激进的少壮派已经摩拳擦掌,希望把言语付诸实践。穆罕默德试图平息态势。在1963年二月的全国组织大会上,他号召独立开展黑人政治运动,但旋即食言,并撤回了一系列其它介入行动,保持抽离立场。当“自由当下党(Freedom Now Party)”于六个月后建党时,穆罕默德更拒绝为其背书、禁止“黑人穆斯林”成员加入。
马尔科姆在1963年十一月肯尼迪遇刺后站出来发表的评论,成为了决裂的导火索。穆罕默德将马尔科姆噤声,又故意停止其所有组织事务,意图羞辱他一番。不过,这只决裂的直接导因,而非根本原因。双方分手的根本原因在于黑人群体中不断涨潮的激进思想和群体行动。面对清真寺门前激愤的群众,这两派“黑人穆斯林”渴望以新的姿态做出恰当回应。
成长与进步
无论到来还是离去,马尔科姆与“黑人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都是建设性的。马尔科姆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投向了“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监狱的肉体隔绝,还有与社会和其族群间的隔绝。多年来,马尔科姆对组织做出了贡献,组织也让马尔科姆受益匪浅。作为替穆罕默德解决问题的头马,马尔科姆得以周游全美,得到了对贫民区黑人身份入木三分的理解。“黑人穆斯林”拓宽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头脑。
马尔科姆的到来是因为孤单和迷茫,而离开则是因为他深入地接触、了解过了黑人群体,不再满足于“黑人穆斯林”的目标和期许;是因为他正成为愈来愈多寻求变革的人眼中的代言;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新使命,或者说,新的使命找上了他。在生平历练的驱使下,无论这份使命困难几何,他都义不容辞。
离开想必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想想吧:在三十八岁的年纪,身旁妻女环绕;工作有保障,待遇不错,供车供房还补贴开支;受人敬仰;在工作中仅一人之下,上司还已年逾古稀、身体抱恙。这样的生活让别人来选,多半会走安稳的道路。专注份内,明哲保身,韬光养晦。毕竟,这才是正统的美国生活方式——不管是在商界、政府、教会、社团还是劳工群体。
改变的实质
但马尔科姆生性并非如此。穆罕默德和手下的牧师一边以严苛的教义要求“黑人穆斯林”信众,一边却宽于律己,简直如同清教传教士。这让马尔科姆十分困扰。他曾想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专注于外界正发生的黑人运动。为了肩负起对黑人群体的真正责任,“黑人穆斯林”需要采取新的,更大胆、激进的方针。但其他认识到需要变革的牧师却慎终如始——他们不是马尔科姆·X。
在1964年初,马尔科姆经历了第二次“重生”。他意识到,自己的归宿在于黑人群众,而非穆罕默德的组织。作为“黑人穆斯林”领袖,他一度选择与腐朽的美国社会背道而驰。现在,他超越了单纯的“拒斥”(一种否定、消极的立场),进而选择与其抗争,组织运动以求变革(一种肯定的、积极的立场)。这是马尔科姆此次改变的实质。
一些极左派黑人团体不理解马尔科姆,嗤笑其变得“软弱”,反而是美国统治阶级和代言人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于是,他们对单飞的马尔科姆变得加倍凶恶。当马尔科姆开始筹划一场新运动时,他们的仇恨和恐惧愈发得证。于此,威廉·F·瓦尔德曾评价:“在因刺客的枪弹殉道之前,马尔科姆早已被结党营私的媒体钉上了刑架。”
长期信条
我们曾听过这样一个表达——“新的马尔科姆·X”。这种说法有对有错。自去年三月以来,马尔科姆的理念有增减,也有保留。在讨论新思想之前,我们先对一些贯彻始终的信条做简单的回顾:
黑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自由;
美国的政府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政府,没有带来自由的可能;
自由派黑人和白人提倡的渐进主义无法实现平等;
必须要揭发并反对“汤姆大叔”们;
黑人必须依靠自己,把斗争掌握在自己手中;
黑人必须自决其斗争的战略与战术;
黑人必须选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领袖;
——在离开“黑人穆斯林”前,马尔科姆就坚持以上观点,一直持续到他辞世之日。
更民主的运动
发起一场新运动是十分困难且劳神的。激进派应当理解并同情这样的任务——同时迎战新旧之敌。从一开始,马尔科姆就表明他不想简单地复制、微调“黑人穆斯林”运动。他想要一种新的架构,一种新的领袖与群众间的联系。
“黑人穆斯林”的一切都以神秘化的领袖和信仰为中心,要求对神圣、全知首领的屈从。马尔科姆的愿景截然不同,从他单飞后第一场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便可略窥一二。他否认自己是“任何领域的专家”,还广开言路,呼唤来自各行各业——尤其是学生,无论黑白——的帮助。
他不只接受建议,更主动寻求建议。他不只诚邀批评,更欢迎批评。我对此有切身体验。我从未与马尔科姆会面,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但我写过关于他的很多文章,其中大多都是对他的声援。他只对其中唯一一篇做过回应并表示感谢,而这恰巧是对他某场演讲评价最为批判的一篇。在我看来,这便马尔科姆的典型作风。
每当读到对组织的一些问题有用或相关的材料时,马尔科姆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其他运动领导人也弄一份,以供一起阅读、思考,进而达到立场上的与时俱进、团结一致。在遇刺当天,他计划参加对其关于“非裔美国人团结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o-American Unity,OAAU)”观点的讨论。显见的是,马尔科姆准备搭建一个架构远比“黑人穆斯林”民主,集体领导程度远高于“黑人穆斯林”的组织。以下事实亦可佐证:尽管令一些保守成员感到不满,但马尔科姆并不害怕与激进派交往,也不会拒绝他们加入组织。
对自己的看法
马尔科姆兼备肢体和头脑的胆识。只有全面地了解了单飞前他对穆罕默德的依从程度,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马尔科姆有多么勇敢。成年后,他与穆罕默德在不只十二年的时间里形同父子——不,还要更深,因为鲜有马尔科姆这般自觉、顺从的儿子。紧接着,马尔科姆瞬间变得孑孑一人。遇刺前三天,他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我曾是‘黑人穆斯林’的代言人。我曾信奉伊利亚·穆罕默德胜过基督徒信奉耶稣。我曾是如此信奉他,以至于我的头脑、身体和言语都百分百地为他和他的运动服务。我对他的信奉又吸引了更多的信众。”话锋一转,他接着说:“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睡梦中,受人控制似的。现在,我的所想、所说都是出于自身,而之前都是按照、遵从伊利亚·穆罕默德的驱使。现在,先生,我自以吾脑思考。”
而这正是我国统治阶级一切力量纠结起来,试图阻碍、防止黑人所做的事——独立思考。你需要来自智力和体魄的胆量,来为自己思考、发声;思考新的主义,寻找被统治阶级禁止的观点;在肯尼亚的茂茂义士与刚果的辛巴战士中寻找它们。独立思考——这才是开放、坦诚、自由的思想和革命领袖的真正标志。
宗教与黑人团结
尽管与穆罕默德分手,但马尔科姆依然信仰伊斯兰教,不过自从去年麦加归来后便仅限于正统教义。即使离开了组织,他始终对穆罕默德赞赏有加。马尔科姆认为——或者说希望——在投身更广阔的黑人运动的同时,亦能避免与“黑人穆斯林”之间的摩擦。马后炮来讲,这种希望其实无端。由马尔科姆·X领导的独立运动是对美国所有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的威胁。不消多时,穆罕默德便展开了无情的中伤攻势,意在孤立马尔科姆。穆罕穆德担心若不及时回应,恐遭自己手下抛弃。如果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对现状造成的冲击、并做出不同应对和准备的话,马尔科姆或许至今仍在我们身边。但对此我们无从、也不得知晓。
无论单飞前后,马尔科姆始终相信黑人团结的力量。但在“黑人穆斯林”时期,他倡导的必然是由穆罕穆德领导、控制的黑人团结,是对组织教规和信条不假思索的遵从。单飞之后,他呼吁的是所有黑人的联合;无论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只要甘愿为自由斗争。
这是一次从宗教派别主义向世俗群众运动的革新。在单飞之初,马尔科姆创立了“穆斯林清真寺公司(Muslim Mosque, Inc.)”,但距离他的理想仍有所亏缺。作为一个宗教机构,穆斯林清真寺公司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迅速纠偏的马尔科姆成立了OAAU。一开始的宗教团体路线表明了他与过往的紧密连接,哪怕已是一年之前;OAAU在数周后的增补则意味着他迅速超越了来自过往的局限。
自卫之问
我们一定要花些时间来谈谈自卫行为;或者按媒体所说——“暴力行为”。纵然本质再清晰不过,媒体依然紧咬此议题不放,所以在此不能不提。
马尔科姆一直支持自我防卫,不论是在混迹于地下世界的青年时代,在“黑人穆斯林”时期,还是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不过在三个时期,“自卫”对他分别有着不同的涵义。“黑人穆斯林”告诉人们,受到攻击就能进行防卫,这是安拉和他的信使所赐之权利。马尔科姆则引用政治和宪法赋权自卫,把神赐的权利带到了人间。“黑人穆斯林”保护的是朋党己见,而马尔科姆则说所有黑人都应该自我防卫。在他口中,自卫权变得明确、具象、现实。马尔科姆对“防卫性来复枪俱乐部(defensive rifle clubs)”的提倡成为了穆罕穆德的首个攻击目标,二人思想的差异也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在座有许多学生,所以我想换种表达方式。我建议你们可以准备一篇题为《媒体对马尔科姆·X在暴力问题上观点的报道》的文章。这必将很有启发。以此话题为例,你们能看清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人是如何获取的“信息”、形成的思想。举一反三,你们还能参透美国整体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受操控的方式——既用宣传替代新闻和事实。
扭曲之幕
至于用何种方法去研究马尔科姆与暴力,我推荐参考中国问题资深记者费利克斯·格林所著新书,《无知之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此书将十五年来中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媒体的报道相比照,得出的结果触目惊心。我在此选读一个典型例子:
“在罗伯特·F·威廉姆斯谏言下,毛泽东曾于1963年就美国种族歧视问题做出过评论,重点内容如下: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而以下则是《基督世纪报(Christian Century)》(以及其它许多美国媒体)对此的报道:
“‘消息从北京传来,毛泽东号召所有有色人种集结,向白人种族开战。此次对全球种族战争的煽动无疑暴露出了他疯子般的仇恨和绝望。’”
如果对我刚才所提的文章题目感兴趣,那你将会格林的书中受益良多,因为马尔科姆在暴力问题上的发言受到了如出一辙的颠倒黑白,且无一不是故意而为。
在座若听过马尔科姆演说便知,他并不宣扬暴力;他支持的是黑人在受攻击时的自卫。他说过一百次,一千次。他说,他反对并希望终结暴力。通过让加害者知道他们必将面对反抗,所有黑人都能帮助终结暴力。但就算马尔科姆再重复说上一百万次,美国报纸的读者也依然无从知晓真相。
《纽约时报》社论
就拿《纽约时报》为例。《时报》理应是全美、甚至全世界最顶尖的日刊,有层次,有内涵,在部分公民自由和权利问题上开明自由。但在我三十年的阅报经验里,《时报》对马尔科姆独独有着不可比拟的恨意。马尔科姆遇刺后,《时报》的伪装滑落了;次日早晨的一篇社论揭露了其丑恶的美国资本主义嘴脸。拉丁谚语有言:“对于死者唯有称美(Speak nothing but good about the dead)。”《时报》对待马尔科姆的态度则是:“对于死者唯有贬损,且若有必要,扭曲事实以毁谤之。”
这篇社论写道:“马尔科姆是一段病史,是一位卓绝但扭曲之人。他将如此多的珍贵禀赋都用于了邪恶的目的。”“病史(case history)”和“扭曲(twisted)”等用词无不在暗示马尔科姆失衡的精神状态。那么,他既是疯狂的,又是邪恶的。
“……他那对暴力残忍而狂热的崇尚……让他声名鹊起,也让他注定终结于暴力。”在《时报》口中,马尔科姆的“暴力崇尚”通过某种莫名的因果关系与日后的死亡相关联;所以,他应当对自己的遇害负责。
“他不曾希望融入社会,也不想融入自己族人的生活……透过那副角质框眼镜,他眼中的世界是扭曲且黑暗的。但借由其对狂热主义的颂扬,他设法将世界变得更加黑暗。而就在昨天,一人正是从他所召唤的黑暗里浮现,将其杀害。”“他所召唤的黑暗”!《时报》的意思是,马尔科姆不仅疯狂、邪恶,还懂得法术——虽然设法拥有三十九岁的面相,但他起码已经三百五十岁,才能“召唤”出种族暴力。在社论结尾,《时报》宽宏大量地让步,称谋杀案件“有待调查”。但不是因为案件的犯罪本质,而是因为“容易触发一场马尔科姆所助长的复仇战争”。
种族主义的逻辑
那么,这种攻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设想,我——或者任何一个所谓的白人——去到市中心,站上一个箱子,说:“白人应当在遭受攻击时保护自己。”我会被打成暴力、种族和狂热分子吗?不会的,我最多会被当作有精神问题。
又如果,另一个白人在我之后上来说道:“如果他们的利益在古巴或越南受到侵犯,白人应该出动入侵部队或一百六十架轰炸机进行防御,”媒体会谴责他为暴力、种族、狂热分子吗?不会。有些人会说,“这自然是理所应当,”另一些人则会说,“那人应该去白宫当差。” 那可不是疯人院,而是白宫。
区别在哪?区别在于,被攻击或被置于攻击之下的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居然有人鼓励黑人自卫,这让美国种族主义绥靖者双目泛红——或者说“泛黑”。他们的反应如此激烈,以至于根本懒得对马尔科姆的遇刺装出半点的愤慨。这两种情况的差异背后,无疑是浸淫整个国家及媒体的种族主义。美国是如此被恐惧和癔症缠身,纵观全球,也只有南非能与之相提并论。
花了如此多时间来阐述再简单不过的真相,这不禁让人难过。这也并非马尔科姆个人哲学的中心话题——只不过最富争议。这是他的纲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除非一个人愿意捍卫他的族群、权利和财产,与恐吓他和噤声他的暴力进行对抗,否则任何人都无法指望能够赢得自由。但这并不是一个核心的要素,其自身也并不是黑人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便黑人如本应和注定地那样组织起来进行自我防卫,他们仍将不得自由。原因是,不平等已经深深扎根于这个社会之中;而这个社会系统本身亦传播、延续着不平等。
种族之问
下面要讨论的是种族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尔科姆经历了非常明显的思想转变,抛弃了“黑人穆斯林”关于种族优劣的谬论和认为白人天生邪恶、堕落的神话。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受到伊斯兰教各族平等的影响,一方面来自与各个国家革命分子的广泛接触。
为了废止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他选择基于具体行为去评价一个人或一场运动,而非依据肤色或种族。要看做了什么,而非说了什么;马尔科姆非常擅于区分二者,尤其当面对白人自由派时(黑人自由派亦然)。他学会了用历史的视角处理种族主义。比如,马尔科姆知道,在经历过环境影响、误导和污染后,美国白人在种族问题上比欧洲白人要更恶劣;所以他会更为提防美国白人。类似的,这种分类法也应用于美国内部的新老代际之间。
在与“青年社会主义联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YSA)”领导人的访谈中,马尔科姆被问到“什么是种族偏见的根源”。他的回答和“黑人穆斯林”的立场迥然不同:“无知与贪婪。”科学社会主义者也许会挪动一下词序,认为是“贪婪与无知”,并由这一主题广泛发散开去;但中心思想是一致的。早先马尔科姆也曾说:“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密不可分。”
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决裂前,为了完成穆罕默德下发的工作,马尔科姆曾短暂旅居国外。但自从1964年单飞以后,他两次造访和途径过非洲与中东地区。在他余下生命中一半的时间里,马尔科姆都在研究、搜寻、探讨、学习,以及寻求和给予帮助。归国之时,他已不只是殖民地革命的同情者,而更成为了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他与世界上受剥削、受压迫的多数人站在一起,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剥削者、压迫者,即他口中国际权力结构内的统治势力。没有人比马尔科姆更决绝、透彻地谴责过美国在刚果的行径。
马尔科姆出游的目的之一自然是动员非洲的支持,好将美国政府以“长期压迫美国黑人”之由送上联合国受审。彼时,美帝国因为刚果暴行在联合国倍遭非洲国家呛声。尽管马尔科姆取得的成果有限,美国国务院依旧把大部分的反对归功——或是归咎——于他。他明白,国务院的眼中钉也是中情局和其它类似机构的肉中刺。在谋杀前一周于底特律听过他演讲的人便知,马尔科姆希望团结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数百万受压迫者,与非裔美洲的兄弟姊妹一起反抗共同的剥削者。
马尔科姆一面开阔着自己的视野,一面对美帝国主义穷追不舍。他出身在黑白隔离的闭塞街巷,却打破、推倒了国家和种族的界限,成为了一名国际主义者。而作为国际主义者,马尔科姆对约翰·基伦斯定义的“爱国者”深以为然:“以尊严为祖国,以人性为领导,以自由为故土。”
政治行动
在政治行动方面,马尔科姆亦遥遥领先“黑人穆斯林”。鉴于“黑人穆斯林”戒绝政治参与,这并非什么难事。他乐见黑人进行政治组织,竞选、选举候选人,淘汰掉由主要党派安插进政府的黑皮肤傀儡。就在离世两个月前,马尔科姆才参加了哈林区一场有关独立政治行动的会议。
但他的政治立场较为笼统。马尔科姆对自由当下党(FNP)的部分工作表示过肯定。去年夏天在非洲时,他曾短暂考虑过藉密歇根州FNP的提名竞选参议员,但最后还是决定在非洲多停留些许。然而,出于未公开透露的原因,马尔科姆从未加入过FNP。他可能认为FNP仍未成熟,抑或立足并非扎实、立命之本太窄。
虽然马尔科姆的政治思想仍待发展,他对资本主义政党和两党制的态度却毫不含糊。对他来说,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这些制度都是黑人的敌人,不配得到黑人的半点支持。对于共产党在1964年给予约翰逊的支持,马尔科姆只有蔑视可言。
马尔科姆并未给社会主义工人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夫顿·德贝里背书,但抨击了德贝里的两个主要对手。以他自己的方式,马尔科姆为徳布里争取到了哈林区选民的支持,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立场。马尔科姆曾说,在一定条件下,他愿意考虑在1965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纽约市长,与两党候选人竞争。尽管马尔科姆在“如何组织独立黑人政治力量”一事上始终没有得出强有力的结论,但就政治光谱而言,他依然会落在偏激进的一端。
结盟之问
马尔科姆遇刺时正做的演讲事关OAAU纲领和一般性的黑人武装运动。就我们所知,他一直在思考结盟的问题,即独立黑人运动与其它国内力量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也知道,他曾在OAAU领导人内部分发过涉及此问题部分方面的文献。
即便不知道这些,我们也能自然地推断出他将涉足结盟一事。只有界定好所有现存和潜在的敌友关系,一个组织才能得到定义,才能明确自己的方针和立场。现在除了猜测,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他就此事的思考结果。不过,有一些既定事实或能引导我们的猜测。
在去年三月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马尔科姆就结盟问题做了如下评论:
“白人可以帮助我们,但不能加入我们。想要成立黑人白人间的联盟,首先至少要有黑人自身的联盟。想要有工人间的团结,首先要有些许的种族团结。在团结起自己人之前,我们无法团结其他人。”
正如我当时所说,马尔科姆并非在否认黑人和白人间工人阶级团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正相反,他在解释如何能在更广泛、更持久的根基上实现工人团结。我想在此多自引一句我曾经的评论:
“社会主义革命者必然赞成(马尔科姆),在形成有意义、互利的劳工-黑人联盟之前,黑人需要首先在规模和意识形态上独立、强势地组织起来,以确保其利益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或多个盟友的裹挟或出卖。”
在他日后的海外旅途中,结盟问题想必反复地出现。在这期间,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马尔科姆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但立场依然坚定。去年五月,他在纽约“武装劳工论坛(Militant Labor Forum)”座谈时讲到:
“在最近于非洲和其它国家的旅行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所有民族——包括黑人和白人——之间齐心协力的重要性。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黑人自己必须首先团结起来。”
据我所知,马尔科姆一直坚持着这一立场。他不反对与包括劳工在内的其它力量结盟,但前提是结成的联盟是有益的;联盟内部的黑人也应独立组织,这样一旦联盟变质,黑人便能通过退出以免遭出卖。
只要满足此二前提,马尔科姆定会赞成独立黑人群众运动与激进劳工运动结盟,对此我毫不怀疑。因为即便是在这两种形式的运动尚未成型的当下,他也愿意在一定条件下与激进白人展开合作。如我所言,像马尔科姆这样乐见与少数派激进势力合作的人,除非失去理智,否则必不会拒绝与大规模激进派联手。随《纽约时报》和《穆罕默德之声(Muhammad Speaks)》怎么说,马尔科姆可没有失去理智。
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接下来,我们简要谈谈马尔科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他曾在《青年社会主义者》采访中说到:
“资本主义没有存续的可能,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吸血’的需求。曾经的资本主义好像一只老鹰,但现在更似一头秃鹫……
只能从无助之人身上吸血。随着全世界各民族的解放,资本主义的猎物会越来越少,吸血的目标也会越来越少,它自己则将越发衰弱。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在资本主义是否会、或是否注定会崩溃一事上,马克思主义者或许尚有疑虑。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生命中最后几个月里,马尔科姆坚定地走上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道路。
马尔科姆没有通过阅读马克思来学习的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他曾设法去学习和了解。他的了解来自反殖民革命,尤其是其中亲社会主义的成分。他与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过探讨,也接触过加纳、几内亚、桑给巴尔和包括美国在内其它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当在去年五月的武装劳工论坛上被问及“想要怎样的政治制度”时,马尔科姆答到:
“我不知道,但我的立场灵活。不过正如早先说过,当今从殖民主义桎梏下崛起的国家无一不在转向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并非巧合。殖民国家多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当今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即是美国。现如今,一个相信资本主义的白人必然同时相信种族主义。假若没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将不复存在。当你同没有种族主义的人交谈,而他们的某种哲学让你相信种族主义不存在于他们的思想中,那么通常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者他们的政治哲学是社会主义。”
克里夫顿·德贝里当时与马尔科姆同是发言嘉宾。他进一步置评了“灵活立场”的效用范围:可以作为一种战术,但不能影响原则,即资本主义制度和政党是自由、正义和平等的敌人。于此,马尔科姆回复:“这是这个问题上我所听过最智慧的答案。”
我认为可以说,马尔科姆之遗产不只是单纯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亦是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我不是称他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彼时并非如此。至于他原本是否会同卡斯特罗后期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只能猜测。但显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同SWP与YSA之关系
我简单谈谈马尔科姆与革命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间的关系:
我们对马尔科姆的态度记载得一清二楚。当他还在“黑人穆斯林”时,我们就把他视为抗争运动中最有天赋、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独立筹划运动时,我们则将其视为一次可能将斗争领向胜利重大发展,并向其公开承诺帮助。为此,我们遭到了一帮所谓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口诛笔伐;仅仅因为支持马尔科姆的运动,我们内部的白人成员就被污作“白皮黑人民族主义者”等种种骂称。这些发生时,马尔科姆还未对社会主义有过半点美言。在当时大多数所谓激进派那里,马尔科姆仿佛宁死也不愿与白人有任何牵连,哪怕是革命派白人。
然后是马尔科姆对我们的态度。当还在“黑人穆斯林”时,他就经常购买《武装者(Militant)》杂志。马尔科姆后来说,他在当时就已经在敦促黑人阅读《武装者》。与穆罕默德决裂后不到一个月,他便在纽约武装劳工论坛上公开称赞《武装者》的求真立场,并祝愿杂志成功。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两次出国归来后,马尔科姆都会做客武装劳工论坛。其中第二次甚至在计划之外:马尔科姆的秘书詹姆斯·沙巴兹本是客座嘉宾之一,但马尔科姆临时致电,询问能不能替代沙巴兹出席;那当然可以。
在大多数OAAU的集会上,马尔科姆都会提一嘴《武装者》,尽管我们从未刻意为此与他沟通。他为杂志在哈林区摊位和商店的出售铺平了道路。在一月份接受《青年社会主义者》采访时,他与YSA的领导人讨论了于今年晚些时候同YSA合作,开展全国校园巡回演讲的可能性。若成行,马尔科姆几乎肯定来到“尤金·维克多·德布斯”礼堂,在“周五晚社会主义者论坛”上发言。他的组织欢迎SWP和YSA黑人成员的加入,也欢迎为《武装者》工作的白人参加OAAU集会。
合作的根基
可以看出,我们有着融洽且互惠的关系。就我方来说,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自视与马尔科姆站在同一立场,有着共同的敌人,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在我们1963年的大会决议中,SWP称黑人民族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不仅能够共存,更相辅相成;二者应当通过思想和行动联系得更加紧密”。我们预测这将在未来实现,且对马尔科姆和我们而言,这似乎已经箭在弦上。
就马尔科姆来说,我认为,合作得以开展是因为他察觉到不同于自由派、共产党、社会主义党和大多数白人激进派,我们并不希望将他的、所有黑人的斗争置于次席,从属于政府、民主党、美国劳工官僚、非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特权官僚,或者其他任何人。他明白,我们一直希望黑人运动取得纲领和行动上的完全独立,能够以自身利益为本、沿着强硬的激进路线自主地发展下去。
纵使再不受欢迎,我们始终恪守原则,向马尔科姆展露出了一片赤诚。他对我们的立场和真心深信不疑,而我们间的合作也就上不封顶。我想强调,只要一个激进组织——哪怕不以社会主义为纲——独立于政府且反对资本主义,马尔科姆都愿意与其携手共进。
黑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
现在,让我们不妨以马尔科姆在生命中最后一年所持的部分观点来为讨论收尾,检视他在黑人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上的立场。这样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少政敌已经开始散布关于马尔科姆的谣传,称其本已处在变节投敌的边缘等等。同时也因为他在最新一期《青年社会主义者》专访中的评论亦给其同黑人民族主义的关系增添了复杂性。
黑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绝非一物,但常常不幸被混为一谈。分离主义提倡黑人从社会中抽离,在美洲或者非洲独立建立黑人国家。黑人民族主义则提倡黑色人种作为同一民族团结一齐,建立由黑人领导、把控,有时独由黑人构成的大小组织,发动斗争,获得自由。现存的黑人民族主义并不涉足任何未来独立建国的问题,不支持也不反对。尽管分离主义者都是黑人民族主义者,但黑人民族主义者并非都是分离主义者。
关长期被误解的二者间区别,可详见社会主义工人党1963年大会决议中《自由当下:黑人解放斗争的新阶段(Freedom Now: The New Stage in the Struggle for Negro Emancipation, Pioneer Publishers)》一文。
关于分离问题的立场转变
在“黑人穆斯林”时期,马尔科姆毫无疑问支持分离主义。在去年三月单飞后的第一场发布会上,他说自己准备发动一场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且重点强调了“黑人民族主义”。但马尔科姆也提到了分离主义。他说自己依旧将分离建国视为“最优解决方案”;不过之前,他都将此称作“唯一解决方案”。“但是,”他接着说,“在非洲分离建国是远期目标。在远期目标实现之前,美国国内仍将存在两千两百万的族人,他们都需要更好的食物、衣着、住房、教育和工作。现在就要。”
彼时,我将此视作马尔科姆的一次宣言,意说明其希望通过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来团结黑人,争取即刻需求;与此同时,继续坚持以分离建国为终极目标,辅以相应的宣传攻势。但我显然理解有误。因为在三月的发言后,再无处觅得任何马尔科姆对黑人独立建国的倡议。五月二十一日,在结束非洲旅程仅数小时后的一场发布会上,马尔科姆对“是否认为黑人应当返回非洲”一问做出了回答。他说,他认为黑人应当留在美国,为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斗争。
或许马尔科姆认为,尽管分离建国令人向往,但虚无缥缈以至于多提无益。或许他认为在分离问题上的两极立场会阻碍黑人团结。又或许他不再将分离建国视作理想。无论如何,在与“黑人穆斯林”决裂当时、或不久以后,马尔科姆就不再是一名分离主义者了。
关于黑人民族主义的回答
那么,马尔科姆在黑人民族主义上持何种立场?无论敌友,人人皆称马尔科姆为民族主义者。直到几周前,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紧接着,他在《青年社会主义者》专访中被问到:“鉴于你常被认为是黑人民族主义者,你会如何定义黑人民族主义?”
他首先这样回答:“我曾将其视作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黑人社群的政治、经济以及种种应当由黑人自己把控。”也就是说,他曾依传统视角定义黑人民族主义,亦如我方才所说。
马尔科姆的第二段回答有关去年五月同加纳一位阿尔及利亚白人革命者的探讨。这位革命者希望让马尔科姆认识到,他自持的黑人民族主义立场恐怕会疏远一部分“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他们亦致力于用任何必要之手段推翻现存的剥削制度”。这部分可由大家自行于《青年社会主义者》中查阅。第三段也是最后一段回答如下:
“那么,我有必要进行大量思考,重新审视我对黑人民族主义的定义。我们能否把黑人所面对问题的解决办法用黑人民族主义简单概括?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我数月以来都没再用过‘黑人民族主义’一词。至于这个国家的黑人解放需要何种总体哲学,我依然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定义的再审视
请注意:他彼时是在重新审视黑人民族主义的定义,且在思考其被概括为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马尔科姆暂停使用了此表达,但尚未找到新的定义作为黑人解放的必要哲学。现在,我想谈谈我个人的解读。
马尔科姆一直是名黑人民族主义者——这是他所有思想的起点,也是他力量与活力的来源。无论他在对自己和亟待拟定的纲领的称呼一事上有多么迟疑,马尔科姆至始至终都是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若把他的本质与他脑海中对自我本质更贴切的指称二者相混淆,那将是一大错误。
黑人族群当前最紧急的需求依然是将广大群众动员、组织起来,组成独立运动并为自由而斗争。而正因为对斗争过程和独立构建运动的贡献,黑人民族主义仍有高度的进步意义。
但黑人民族主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黑人民族主义有可能是得到答案的必要手段,但不是答案的全部。它能帮助构建一场独立运动,但不一定能提供通往胜利的纲领。
“黑人民族主义”加上……
要黑人民族主义,没错。但解法不能被局限地概括为黑人民族主义。所需要的是黑人民族主义加上根本性社会变革,是黑人民族主义加上全社会的转型。尽管马尔科姆艰难地寻找着正确的指称,但实际上,他正在成为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加“革命者”(从《青年社会主义者》的专访来看,马尔科姆对“革命者”一词有着无上尊重)。
若说黑人有获得自由平等的可能,那便有且只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注意,我所用词仅是获得自由的可能)是渐进主义;和平改革;十年时间内这一点、那一点的局部修补。不是“自由当下”,而是“自由未来”;而对于生活在当下的黑人来说,“自由未来”意味着“自由永无”。这即是林登·约翰逊、沃尔特·路德、马丁·路德·金、罗伊·威尔金斯和贝雅·鲁斯丁所持之纲领。如我们所知,马尔科姆断然拒绝了这种方法。
第二种是通过分离,通过向非洲或者美国部分地区移民实现。如我指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马尔科姆后来放弃了这种方法。
第三种——只有这三种,别再无它法——是通过对社会的革命性重构实现,基础性地改变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法律、教育系统;通过由反对并旨在根除种族主义的势力会组成新的政府,以革除现行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
新的结合体
从之前所引之马尔科姆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评价不难看出,他倾向于第三种方法,或者至少开始加以关注。至于能否成功和如何实现,马尔科姆并不确定,但在加以思考;他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将这条路线纳入OAAU的纲领与活动当中。
我认为,这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他在自我指称上的踌躇。因为马尔科姆不再只是黑人民族主义者,而是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加社会革命家,或者即将变成如此。
社会主义者们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自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者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融合的趋势;此种始发自民族主义的转变可见于古巴卡斯特罗及其运动之中。我们已经向许多反对派指出,在美国这类国家中,黑人民族主义必然在社会、政治层面取得最先进、最激进的成果。因此,我们向来主张、判断,黑人民族主义者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能够、应该且终将携手合作。
马尔科姆对指称的迟疑来自于新的实践——他正走向黑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这种结合适用于美国国情,并为贫民区的黑人群众所接受。马尔科姆未能在遇害前完成这项工作。现在,要由其他人来接手他所开创的事业。
终有后继
现在他死了,在可能是生命中最重要、最有成果的一年离开了我们。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这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正如弗兰克·洛弗尔上周在非裔美国人广播公司(Afro-American Broadcasting Co.)的追悼会上所说,对黑人和所有希望根除孕育种族主义之制度的美国白人而言,马尔科姆之死是一次巨大的打击。马尔科姆这类人并不世出,当世罕有。人类进步的敌人将得益于他的离世,而向着进步的斗士则会遭到削弱和伤害。
但尽管打击巨大,斗争不会被彻底摧垮。要顶替马尔科姆绝非易事,但后继终将有人。资本主义制度在滋长种族主义的同时,也诞生了对种族主义的反抗,尤其是在青年当中。马尔科姆不会在一夜间得到替代,不过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都应该加倍努力地奋斗、工作、斗争,加倍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填补这位被我们所爱戴之人身后留下的空缺,并扶持、鼓舞那些终将继承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