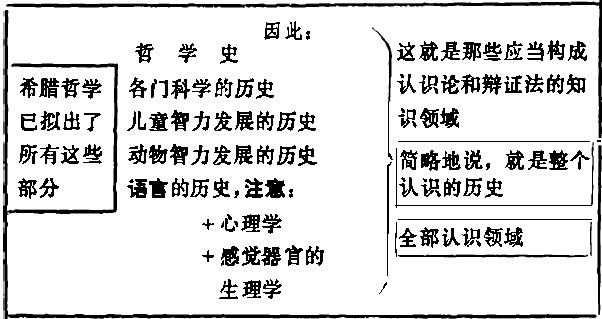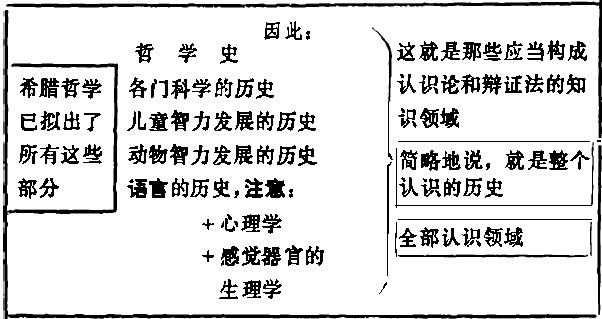〔
说明〕摘自《关于艺术的对话: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吴谷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部分标点及外文有修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已收录本文的前六节
[1](人民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但缺少两节,故于此补充。
此外,本文注释中的《列宁选集》、《列宁全集》版本不详,无法核对。
“……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当做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主观主义的社会学者的议论似乎从‘个人’开始,其实是从下面这点开始的,就是把他认为合理的(因为他把自己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从而他就没有可能研究他们的实际的思想和感情)‘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些人身上,换句话说,‘是从空想开始的’……”
[20]列宁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原理,应用于文学上,就是指出:眼前有“真实的个人”的文艺学家,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不应当从似乎作为起因的这种个人来开始自己的研究。他应当从社会关系开始,因为只有这种研究才为真正理解个人提供了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