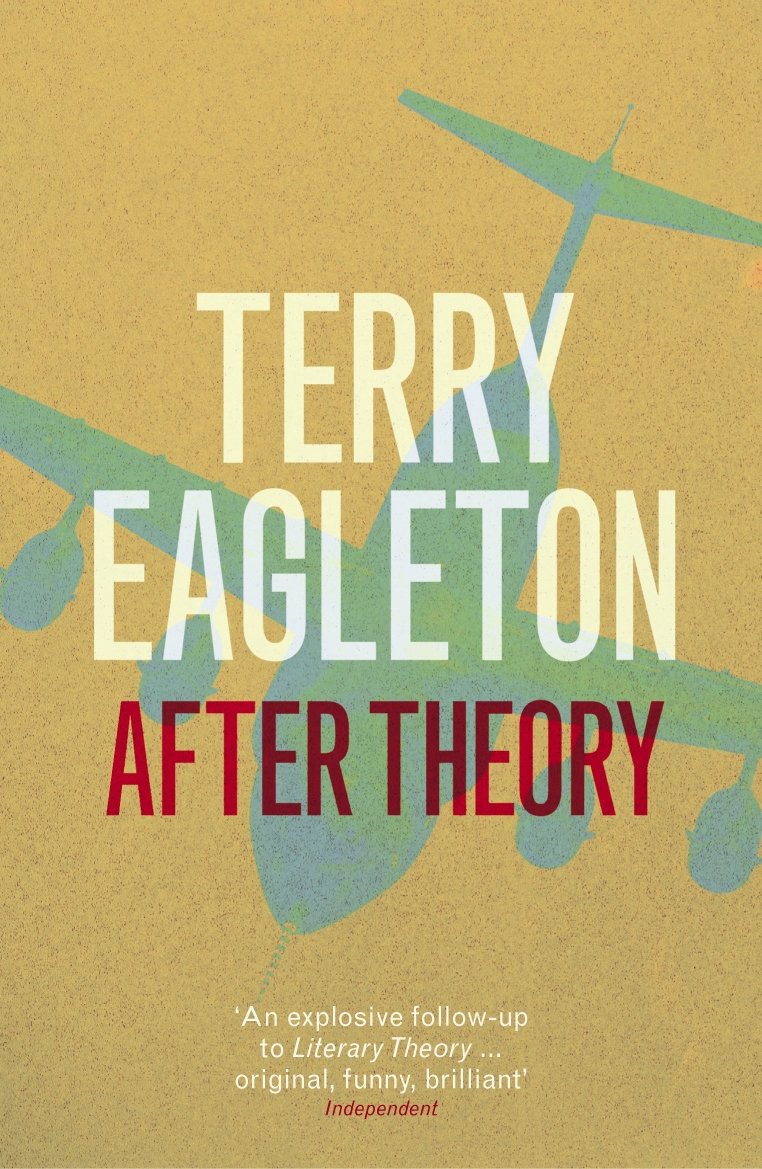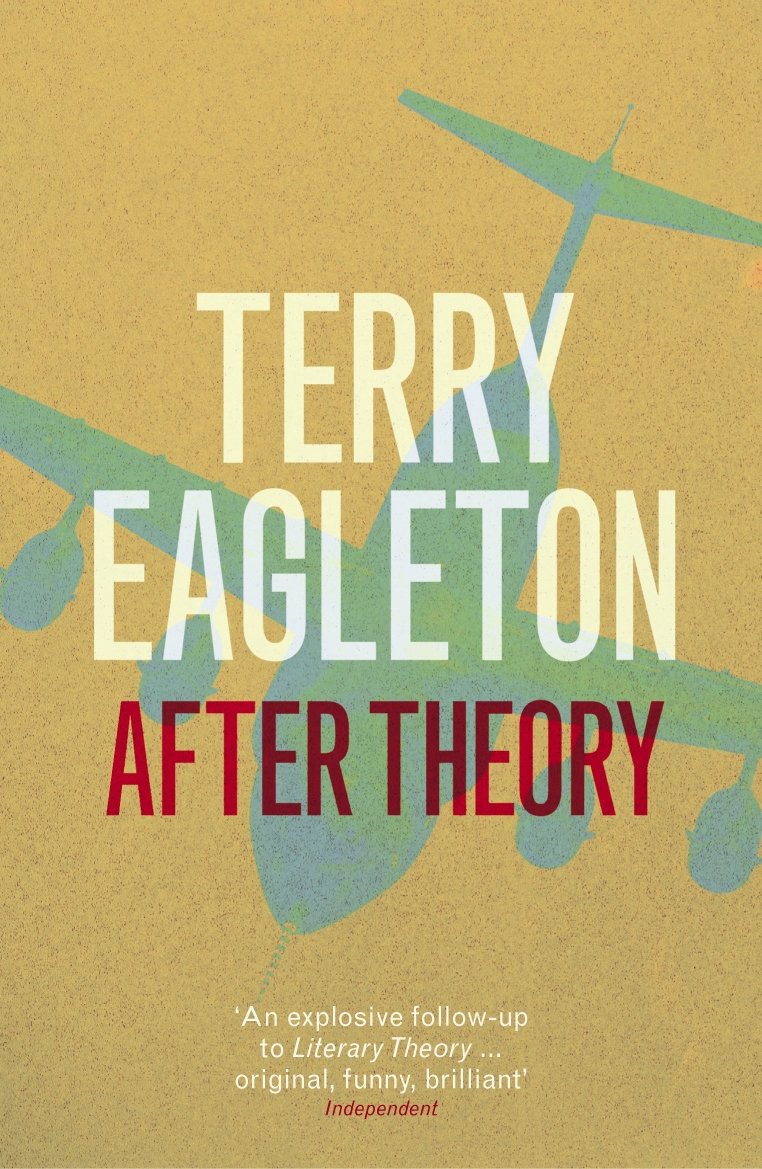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密不可分的。伦理学论述如何善于为人,但没人能单独做到这一点。此外,除非存在着允许你这样做的政治机制,否则任何人都做不到。马克思继承的正是这种道德思想……善恶的问题被错误地从它们的社会背景中抽象出来,而又不得不回归于社会背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就是经典意义上的道德学家。他相信,道德探索必须检验组成特定行为或特定生活方式的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或个人的生活方式。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