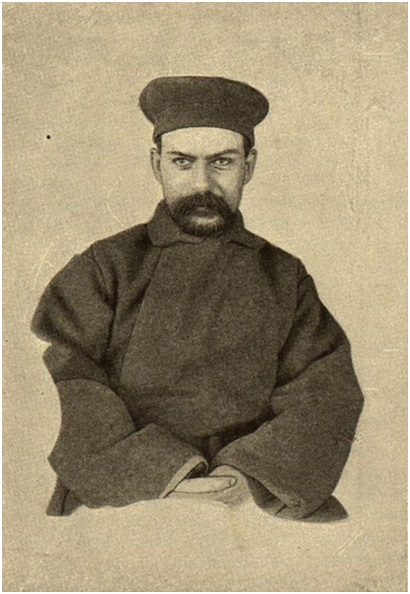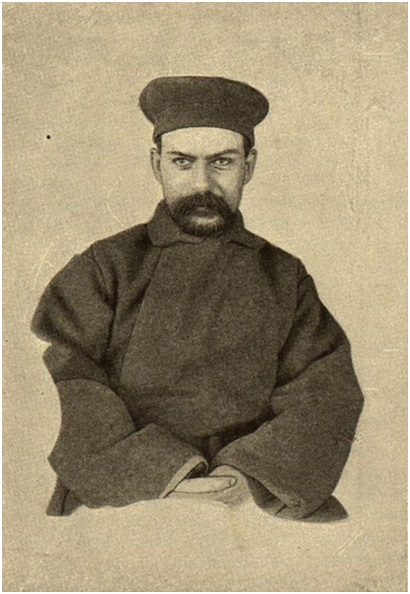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第二十一章 十二月
12月4日,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同意了《财政宣言》。而在12月6日,在莫斯科军区大骚乱的直接压力下,拥有10万工人作为基础的苏维埃决定与革命政党站在一起,宣布在第二天即12月7日起进行政治总罢工,并努力将其转变为武装暴动。12月5—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29条铁路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同意苏维埃的决议。邮政—电报代表大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定。
在彼得堡,罢工于8日开始,次日达到顶点,在12日开始消退。它远不如十一月罢工那样齐心协力,参与的工人不到三分之二。这种犹豫不决可以被解释为:彼得堡工人已经清楚意识到,这并非一场罢工示威,而是生死攸关的斗争。1月9日在群众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面对规模庞大、以禁卫团为骨干的卫戍部队,彼得堡工人没法主动发起革命起义;他们的任务,正如十月罢工表明的那样,是趁全国其他地区起义动摇专制主义的时候,给它以最后一击。各省的重大胜利是彼得堡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基本心理前提。但是,这样的胜利没有到来,退缩代替了犹豫不决。
除了彼得堡的消极态度以外,尼古拉耶夫铁路(彼得堡—莫斯科)的继续运行也致命地影响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在首都普遍占主导地位的观望情绪影响了铁路工会的彼得堡委员会。与此同时,政府紧盯着这条动脉,利用这一耽搁,出动军队占领了这条铁路。部分车间坚持罢工,但电报已经落入了当局手里,而线路则由铁道营直接管理。罢工的工人已经多次尝试阻止交通,但都徒劳无获。12月16日,特维尔工人破坏了部分铁轨,以阻止军队从彼得堡向莫斯科进发。但这已经太晚了:谢苗洛夫禁卫团已经过去了。然而,总的来说,铁路罢工的开展是非常团结的。大多数线路到10号之前就已经开始罢工;其余线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在宣布罢工开始的同时,铁路工会的会议宣布:“我们承诺比政府更快地将部队从满洲送回家……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将粮食送到饥饿的农民手里,并补给铁路线上的同志。”这里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遇到了类似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正是尚有思考能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想想其意义的:在瘫痪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总罢工将极其重要的国家职能转交给自己的组织。而且,必须承认,铁路工会总的来说做得非常好。尽管许多地方附近就有政府军,但运送储备物资、纠察队员和革命组织成员的火车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和准确率运行着。许多车站是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员管理。铁路建筑物上飘扬着红旗。第一个罢工的城市是莫斯科。第二天,彼得堡、明斯克、塔甘罗格开始了罢工。紧接着,在大城市中——第十日梯弗里斯[1],第十一日维尔纽斯,第十二日哈尔科夫、基辅、西诺夫哥罗德,第十三日敖德萨、里加,第十四日罗兹,第十五日华沙。总共33个城镇参与了罢工,与此相比的十月则是有39个城镇。
12月运动的中心是在莫斯科。
12月初,莫斯科军区的一部分团就已经开始了骚动。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作出了种种的努力来防止各种孤立的爆发,但骚动仍然仿佛像决口的河水。工人当中出现了高声呼吁:“必须帮助士兵,不能贻误战机。”守卫工厂的卫兵也完全受到了工人的影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这讲的:“你们一起义,我们也就跟着起义,并打开军火库!”12月4日,部队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而这个苏维埃也向工人苏维埃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从其它城镇也传来了模糊但持续的谣言,说军队将加入工人的行动。这就是莫斯科罢工开始时的气氛。
第一天大约有10万人停止了工作。两名司机试图将火车开出车站,其中一个被杀。城里零零散散的地方发生了小冲突。一队民众纠察队抢光了武器店。从这一天起,在莫斯科街头设立的普通警察岗哨消失了。警察只成群成群地出现。第二天,罢工人数增加到了15万。莫斯科的罢工变得具有普遍性,并蔓延到了郊区的工厂。到处都是大规模集会。在远东列车的终点站,人群解除了刚从满洲回来的军官的武装。从一辆铁路货车上,工人取走了几十包子弹。后来,他们又从其它车厢上取走了武器。
12月8日,也就是罢工的第二天,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决定:“当部队出现的时候,就设法与士兵交谈,用同志式的语言影响他们……暂时避免公开冲突,并只有在部队做出挑战性行为的时候才进行武装抵抗。”大家都明白,军队将一锤定音。关于军区情绪的最微小的鼓舞人心的传言也在口耳相传。一直以来,革命群众都在与莫斯科当局为争取军队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
例如:一些印刷工人听说一队步兵在《马赛曲》的旋律中沿街行进,便代表去迎接。但为时已晚。军事长官用哥萨克兵和龙骑兵团团包围了这些兴奋的士兵,把他们赶回了军营,然后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就在同一天,一名警官指挥的500名哥萨克接到了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哥萨克拒绝服从,与群众交谈。随后,在一名军士的命令下,他们调转马头,在群众的友好呼喊声中慢慢离开。
上万工人的示威撞见了哥萨克。发生了普遍的慌乱。人群中出现两名女工,带着红旗,扑向哥萨克。她们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宁死也不交出旗帜!”哥萨克被吓着了。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人群感受到了哥萨克的动摇,向他们施压道:“哥萨克,我们手无寸铁,难道你们会向我们开枪吗?”哥萨克回答道:“你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就也不向你们开哩。”吃惊而狂怒的军官发疯地骂人。但是晚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人群的愤怒呐喊声之中。有人作了简短的演讲。人群在欢呼声中将演讲者抬起来。没几分钟,哥萨克肩头扛着枪,调转马头,飞奔而去。
军队团团包围,对手无寸铁的人群进行的了大屠杀,于是人民的集会结束了。在这之后,城镇弥漫着更加紧张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挤上街。谣言四起,不曾断绝。每分每秒都与死神擦肩而过。所有人的脸上显露着幸福的激动,但也掺杂着不安的情绪。高尔基那时在莫斯科,写道:“许多人认为,街垒是革命者开始建造的;这对革命者来说,当然是至上的荣幸,但却是完全不公平的——街垒一开始的建造者,正是普通人,非党的人,事件的要点也在于此。第一批街垒在特维尔街[2]上,是在欢声笑语中轻而易举地建成的;而在这个快乐的工作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参与——从有声望的、穿着昂贵大衣的老爷,再到女厨子和看院人;而这些人不久以前还是当局的‘坚固支柱’。龙骑兵向街垒齐射,死伤若干人——愤怒的哀嚎、齐声的呐喊在空中回荡,一切都改变了。在齐射过后,普通人放弃了原先的轻松心态,开始认真地建造街垒,希望在杜巴索夫[3]及其龙骑兵的枪口之下用它来保卫自己的生命。”
工人纠察队(Дружинник),也就是革命组织的军事化武装分队,变得更加活跃了。他们系统性地解除了遇到的每一名警察的武装。就在这里,“举起手来”的要求第一次开始实践,目的是为了确保突袭者的安全。谁不举起手,他们就杀死谁。他们不碰士兵一根手指头,以防疏远他们。有那么一次集会甚至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凡是没有指挥者的命令就开火的人,将会被处决。工人在工厂和车间旁鼓动士兵。但到了第三天,罢工开始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例如,一群龙骑兵在因罢工而陷入黑暗的广场上驱散了一个晚间集会。“兄弟们,别碰我们,我们是一路人!”士兵从旁边经过离开。但过了一刻钟后,他们以更大的人数返回,并向人群发起了攻击。黑暗,恐慌,呐喊,咒骂;一部分人群在一个有轨电车亭里寻找掩护。龙骑兵要求对方投降。遭到了拒绝。他们齐射了几次,打死了一名小学生,打伤了几个人。要么是良心的驱使,要么是害怕报复,龙骑兵飞奔而去。“杀人犯!”人群站在第一批受害者旁边,愤怒地握紧了拳头。“杀人犯!”刹那间,血迹斑斑的亭子化为火海。“杀人犯!”人群为发泄自己的情绪寻找出气筒。在黑暗中,在危险中,他们前进,遇到障碍,继续进逼。枪声再次响起。“杀人犯!”人群开始筑起街垒。他们从未干过这种工作,因此工作进行得很笨拙,且没有条理……在同一片黑暗中,三四十人齐声合唱“你们已英勇牺牲”……又有齐射,又有死伤。相邻的院子变成了急救站,住在附近的居民充当看护士,守在门口。
随着军事行动的开始,社会民主党战斗组织在整个莫斯科张贴了一张呼吁书,其中向起义者给出了下列技术指示:
“1.首要原则:不要成群行动。以三人或四人的小队伍行动,不能过多。但是要尽可能增加这种小组的数量,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学会快速突击和快速消失。警察在试图调动一百个哥萨克的队伍向上千的人群开火。你们需要让那一百个哥萨克面对的敌手变成一两个零星的射手。打一百个人比打一个人更加容易,特别是如果这个人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开火,然后又消失,来无影去无踪。
2.除此之外,同志们,不要占领坚固的位置。军队总是会夺回它们,或者干脆用炮火来摧毁它们。让我们的堡垒,变成前后都有入口的院子,以及所有容易射击并容易撤离的地方。即使他们占领了这样的地方,也会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而自己却损失惨重。”
革命者的战术是由形势本身迅速决定的。与此相反的是,政府军在整整五天的时间里,完全地暴露出自己对对手战术的不确定性,并表现出了嗜血的野蛮性、迷茫和混乱的混合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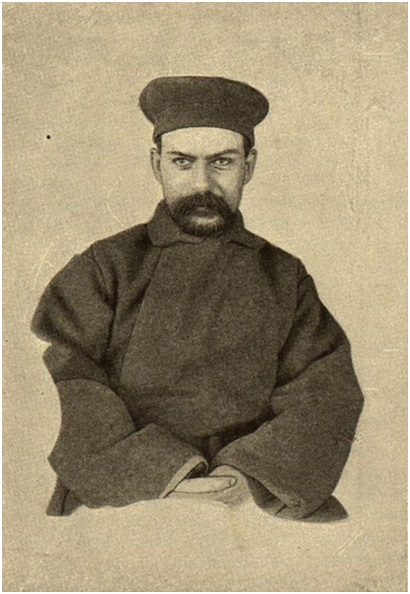
(斯维尔奇科夫,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身着囚服照)
接下来是一场战斗的例子。有24名射手,组成了一个最勇敢的格鲁吉亚战斗队。三三两两地公开前进。人群提醒他们,有16个龙骑兵和其军官正在朝他们的方向前进。战斗队停下来列队,拿起毛瑟枪,准备进行战斗。骑兵部队一出现,战斗队就进行了齐射。军官受了伤,马匹也受了伤,前蹄腾起。骑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无法还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战斗队打了近百发子弹。龙骑兵留下了几个死伤者,被战斗队打得仓皇逃窜。人群敦促道:“现在就快走吧,他们把大炮拉过来了。”确实,大炮很快就出场了。第一轮齐射在人群中造成了数十人死伤,而他们却从未想过会遭受炮击。而在这时,格鲁吉亚人已经在另一个地方对军队展开了另一轮射击……战斗队几乎无懈可击,因为他们披上了普遍同情的铠甲。
下面还有一个例子。一个由13人组成的纠察队占据了一栋大楼,他们在500—600名士兵的枪林弹雨中坚守了4个小时,总共也就有3把步枪和2门机枪。在用光弹药并给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他们毫发无伤地撤退了。而士兵们用炮火摧毁了几个街区,烧毁了一些木质房屋,杀死了一些惊恐的居民……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赶走一些革命者……
街垒没有得到防御。这些街垒只是阻碍了部队的——特别是龙骑兵的行动。在街垒区,房屋在火炮的范围之外。部队只有在向整条街开火以后,才会“占领”街垒,以确保它们后面没有任何人。当士兵一离开街垒后,它就被恢复了。杜巴索夫的炮兵是从12月10日开始系统性射击的。步枪和机枪不知疲倦,扫射一条又一条街道。牺牲者不是按个位数记的,而是以数十人计算。愤怒不安的人群跑来跑去,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士兵们不是向单个革命者开火,而是向名为莫斯科的模糊敌人开火——往它那住着老人和小孩的房屋,它那手无寸铁的街头人群开火……“杀人犯!胆小鬼!你们就是这样来恢复自己在满洲的荣耀的!”
在第一次炮击后,街垒的建设工作变得热火朝天。规模更大了,方法也更加大胆了。人群推倒大水果摊,推倒报刊亭,拆掉商店的招牌,砸碎生铁栏杆,拆掉有轨电车的架空电线。
反动报纸报道说,“他们无视了警方所有门都应该上锁的命令,把许多的房门都拆掉了铰链,用来修建街垒!”到12月11日,整个城市的主要地区都已经被街垒网给覆盖了。整条街都被包裹在有刺铁丝网中。
杜巴索夫宣布,只要遇到成群结队“超过三人以上”,都会进行开火。但龙骑兵也会向落单的人开火。首先他们会进行搜查;如果找不到任何武器,就会放走,然后朝他们背后放枪。他们甚至还会朝看杜巴索夫的公告看呆的人开火。只要有从窗户里有一枪被打出(不少是有奸细开的),房屋就会立即遭受炮火打击。一滩滩的血迹和带着头发的脑浆粘在商店的招牌上面,显示出子弹的路径。许多房屋都被打出了洞。在一栋被毁坏的建筑外(起义者的可怕公关),有一个装着人肉的盘子,上面写道:“请为受害者捐款!”
两三天后,莫斯科军区的情绪就变得明显不利于起义了。从骚乱之初,军事当局就在军营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们把后备部队、志愿兵和那些不可靠的人免职,并为剩下的人提供了更好的伙食。一开始,只有最可靠的部队被用于镇压。而那些比较可疑的团,其最有政治意识的成员都被留在了军营里。杜巴索夫在第二阶段才把他们派上战场。起初,这些部队不情愿也没有信心。但是,一颗随机的子弹,或者军官在他们的饥饿与疲惫的基础上进行的教唆,可以促使他们采取可怕的、过度残忍的行为。杜巴索夫通过大量的官存伏特加加强了这些影响。龙骑兵从头到尾一直是半醉的。
然而,游击作战既让他们无能狂怒,也让他们疲惫不堪。居民的普遍敌意让部队士气低落。12月13—14日是危机的日子。疲惫不堪的部队拒绝与他们看不见的、被夸大了的敌人作战。在这些天里,发生了几起军官自杀的事件……
杜巴索夫向彼得堡告知,在莫斯科军区的15000人中,只有5000人可以投入行动,因为剩下的都不可靠;然后还要求了增援。他被告知,彼得堡军区一部分被派到了波罗的海地区,一部分不可靠,而剩下的人他们自己需要用。多亏了从参谋部偷来的文件,这些通信在城镇上广为人知,成为了勇气与希望的有力注脚。但杜巴索夫还是达到了目的。他要求直接与皇村通电话,并宣称自己不能保证“专制制度固若金汤”。命令立即下达,谢苗诺夫禁卫团被派往莫斯科。
12月15日,局势突然变化。谢苗诺夫团到来的希望很快给莫斯科反动团体贴了一剂狗皮膏药。俄罗斯人民联盟从贫民窟里召集来的武装“民兵”出现在街头。政府的活跃力量因临近的城市调来的军队而扩大了。纠察队员筋疲力尽。普通人已经受够了恐惧与不确定感。工人群众的士气开始减退,胜利的希望消失了。商店、办公室、银行、交易所重新开放。街道上的交通开始活跃。报纸开始出版。所有人都觉得,街垒下的生活已经结束了。城里大部分地区的枪声也都平息了。12月16日,随着彼得堡和华沙部队的到来,杜巴索夫已经完全成为了局势的主人。他转守为攻,完全清除了市中心的街垒。苏维埃和党认识到了局势的无望,在这一天作出了12月19日结束罢工的决定。
在整个起义期间,普雷斯尼亚区,也就是莫斯科的蒙马特区,一直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12月10日,当市中心的枪声已经响起的时候,普雷斯尼亚区依然平静。那里的集会按照自己的作息行动,但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了。他们渴望采取行动,并包围住代表。最后,在下午4点,他们收到了从市中心来的命令:建造街垒。普列斯尼亚区开始热闹起来了。在这里,没有出现市中心的那种混乱现象。工人们组织了10人小组,选出了小组长,用铁锹、铁棍和斧子武装自己——就像普通的市政工人一样,有条不紊地走到了街上。没有人无所事事。妇女把雪橇、木柴和大门搬到街上。工人们锯砍电报杆和灯柱。整个普列斯尼亚区响起了斧头的声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森林在伐木。
普列斯尼亚被军队切断了与城市的联系,被街垒网络牢牢地覆盖着。它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营地。到处都是纠察队员在执勤;晚上,武装哨兵在街垒之间踱步,向路人索要密码。最有热情的是女工姑娘们。她们热爱侦查行动,询问警察,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有用的信息。在普列斯尼亚有多少武装纠察队员?大约200人,不可能比这更多了。大约有80只步枪或毛瑟枪供他们使用。活跃力量尽管数量如此稀少,但与军队仍不断发生冲突。士兵被解除武装,反抗的人被杀死。工人们恢复了被破坏的街垒。纠察队员严格遵守游击战术:它们两三人一组,从房屋、木材仓库、空车厢向哥萨克和炮兵射击,然后快速转移,再次向士兵倾泻子弹……12月12日,纠察队员从龙骑兵手里缴获了一门炮。他们围在炮边转了一刻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一支龙骑兵和哥萨克组成的大部队夺回了炮,解决了他们的困惑。
12月13日晚,普列斯尼亚的纠察队俘虏了6名炮兵,并把他们带到了一家工厂。他们被安排在公共餐桌上吃饭。在吃饭期间,有人发表了政治性质的讲话。士兵们带着同情心,专心致志地听着。晚饭后,他们在没有搜查和解除武装的状况下被放了回去——工人不想激怒他们。
12月15日晚,纠察队在街上逮捕了国安单位的领导沃伊洛什尼科夫,搜查了他的公寓,没收了重点监视名单,并缴获了600卢布的国库资金。他被当场判处死刑,在普罗霍罗夫工厂的院子里被枪毙。他平静地听完判决,勇敢地迎接了死亡——死得比活着更高贵。
16日,对普列斯尼亚的炮击尝试开始了。纠察队员以强大的火力回应,迫使炮兵退却。但就在同一天,人们知道了杜巴索夫获得了来自彼得堡和华沙的援军,士气开始下跌。织工开始向乡下逃亡。道路上到处都是背着白色背囊步行的难民。
16日晚,普列斯尼亚被政府军包围在一个铁圈之中。17日早上六点后不久,这些部队就开始了无情的炮击。炮声每分钟多达7次。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中途只有一个小时的喘息时间。许多工厂和住房被毁,陷入火海。炮击是从两边进行的。普列斯尼亚被火与烟雾包围,变成了地狱。房屋与街垒化为火海,妇女和儿童在黑色烟雾中飞奔,空气中弥漫着射击的轰鸣声和劈啪声。火光四射,像白天一样照亮了深夜,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纠察队直到中午12点前都成功抵抗了步兵,但敌人的连续火力迫使他们停止了战斗行动。从这时起,只有一小群纠察队员主动地、冒着风险带着武器留了下来。
到了18日上午,普列斯尼亚的街垒被清除了。“和平的”居民被允许离开普列斯尼亚,部队甚至大意到没去搜身就放走了人。纠察队员是第一批离开的人,其中有一部分甚至还带着武器。后来,士兵横行霸道、大开杀戒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纠察队员留在普列斯尼亚了。
谢苗诺夫“安抚”部队被派去铁路执行任务,得到了命令:“不要进行逮捕,要毫不留情地行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遭到抵抗。没有人对他们开一枪,但他们却在铁路沿线上杀了将近150人,没有调查也不经审判。受伤的人被从医疗车厢上拖下来,然后被彻底打死。尸体躺在周围,画面惨不忍睹。被彼得堡禁卫军射杀的人中有一位司机乌赫托姆斯基,他在机枪的扫射下,用火车头使工人战斗队逃过了追捕。在被枪毙之前,他平静而自豪地对刽子手留下了遗言:“所有人都得救了,你们追不上他们了。”
莫斯科的起义持续了9天,从12月9日到12月17日。莫斯科起义的战斗人员到底有多少?小到不足为提。有700—800人参加了党的战斗队——其中有500名社会民主党人,250—300名社会革命党人;将近500个配备枪支的铁路工人在车站和沿线行动,将近400名来自印刷工人和店员的志愿射手组成了辅助部队。志愿射手组成的小组出现了不少。说到他们,不得不提到四位从黑山来的志愿者。他们是出色的射手,无所畏惧,不知疲惫,成群结队行动,只杀警察和军官。他们中的两人被杀,第三个人受伤,第四个人的温切斯特步枪被毁。这第四个人获得了新的步枪,然后又一个人开始了自己的危险狩猎。每天早上他会获得50发子弹,但他抱怨太少。他陷入了迷茫,为他失去的同志哭泣,为他们的牺牲进行可怕的报复。
那么,数量如此之少的纠察队员,是怎么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和成千上万的卫戍部队战斗的呢?这个革命谜题的答案正是人民群众的情绪。整个城市的街道、房屋、栅栏和大门都加入了反对政府士兵的密谋。百万居民在游击队员和正规军之间形成了一道血肉城墙。纠察队员只有几百人,但街垒的建设与维护是由群众进行的。广大群众以积极的同情氛围拱卫着积极革命者,并尽可能地挫败了政府的计划。这数十万产生同情的分子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并且首要就是工人。除了出卖灵魂的街头虫豸以外,只有最上层的资本家站在政府一边。莫斯科市杜马在起义前两个月还在骄傲地展示自己的激进主义,现在却坚决地站到了杜巴索夫的背后。不只是十月党人古契科夫,而且还有未来的第二届杜马主席戈洛文[4],加入了总督的议事会。
莫斯科起义的牺牲者有多少?确切数字不详,而且永远也无法确定。47家诊所和医院提供的数字显示,有885名伤者和174名死者被记录在案。但那些被杀的人却很少被送到医院;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的尸体躺在了警察局那里,然后被秘密地运走。在那段时间里,有454人被埋进了公墓。但是,有更多的尸体被列车运出了城。如果我们推测说莫斯科起义死伤人数各1000人,那么差距也不会太大。有86名儿童被杀,其中还包括未断奶的婴儿。如果我们还记得,那1848年三月在柏林发生的,对普鲁士绝对主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打击的起义,死亡人数只有183人的话,莫斯科的数字就会更加显眼……政府从未宣布过任何一方的确切损失数字。一份官方报告说只有“几十名士兵被杀或受伤。”但实际上,却应该有几百人。代价不算太高,因为危在旦夕的是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心脏”。
如果我们抛开边界地区(高加索和波罗的海)不计的话,那么对12月的浪潮来说,没有地方能比莫斯科还涨得更高了。不过,街垒、与军队交火、火炮射击也出现在以下城市:哈尔科夫、亚历山德罗夫、下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特维尔……
当各地的起义被破坏以后,围剿队的时代就开始了。就像这一官方名字表明的那样,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敌人,而是报复战败者。在比莫斯科还要早两周爆发起义的波罗的海地区,围剿队被分成了许多小分队,来执行波罗的海的男爵(这是一个由俄国官僚机构最野蛮肮脏的代表组成的种姓)们的嗜血指示。拉脱维亚的工人和农民被枪杀、绞死、鞭打致死、被棍子打,被赶上了绞刑架,在沙皇国歌的旋律中被处决。在两个月里,波罗的海各省有749人遭到处决,100多个农场被烧毁,许多人被用鞭子打死。
就这样,蒙上帝之恩,专制主义垂死挣扎。从1905年1月9日到1906年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根据近似但肯定不夸张的数字,沙皇政府杀死了近14000人,处决了1000多人,打伤了20000多人(其中有许多因伤重而死),而被逮捕、流放和监禁的人就有70000个。这个代价并不过分,因为下的赌注,是沙皇专制的存亡。
[1] 今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中译者注
[2] 莫斯科的一条主干路,正对红场,从市中心直走通向特维尔,因此命名。——中译者注
[3]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杜巴索夫(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Дуба́сов,1845年6月21日—1912年6月1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3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2—1897年任驻柏林大使馆海军特工。1893年晋升为海军上将军衔。1897—1898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01—1905年任海军技术委员会主席。1905—1906年任莫斯科总督,在任期间镇压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1907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06—1912年任国务院议员。1912年逝世。——中译者注
[4] 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文(Фё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ловин,1868年1月2日—1937年12月10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6年起担任莫斯科地方自治局议员。1904年加入解放社。1904—1907年任莫斯科地方自治局局长。1905年参与创立立宪民主党。1907年任第二届国家杜马主席,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主管艺术领域工作。十月革命后曾在全俄援助饥荒委员会工作。此后多次被捕。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