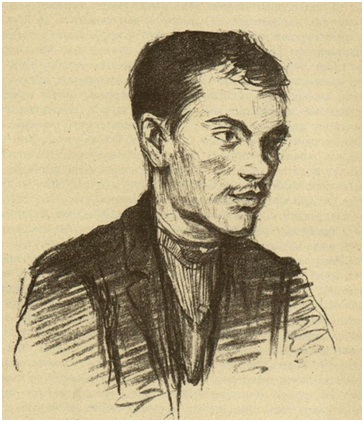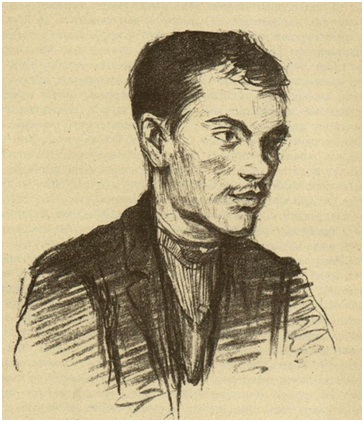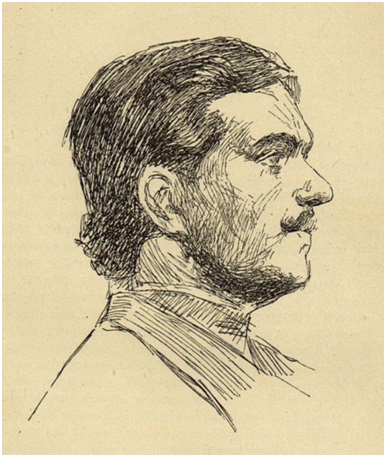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第三章 我在法庭上的发言[1]
(1907年10月4—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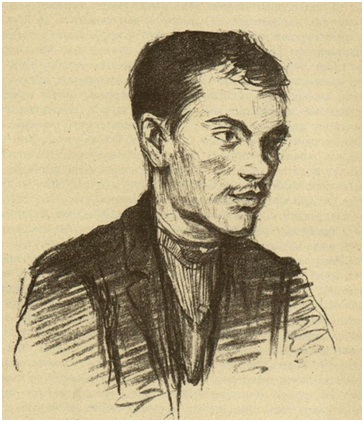
(工人克拉辛,苏维埃案件的被告人之一)
各位法官,各等级的代表!
本法庭的审查对象,同预先审查的对象一样,主要是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存在的50天里,它没有做这件事。无论这个问题在特别审判庭眼中多么的奇怪,它也没在苏维埃的任何一个会议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的任何一次会议都没有提出或讨论过武装起义的问题;不仅如此,任何一次会议都没有提出或讨论过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总罢工,以及它作为革命斗争方法的原则性意义的独立问题。这几年来,首先是在革命报刊,然后是在集会和聚会上围绕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辩论,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却完全未曾研究过这些问题。之后我会解释这意味着什么,并评定工人代表苏维埃对武装起义的态度。但首先,在讨论这一法庭眼中的核心问题之前,我将冒昧地提请法庭注意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加普遍,但又没那么尖锐,即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普遍使用暴力的问题。苏维埃是否认为,在一定情况下采用暴力和高压手段是正当的呢?对于用这样概括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将回答:是!我和检方同样明白,在任何“正常”运作的国家里,无论其形式如何,暴力与镇压的垄断权都属于政府当局。这是它“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它对自己的这一权利采取了最容易吃醋的关心态度,时刻警惕着任何个人团体侵犯其暴力垄断权。国家组织就是以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生存作斗争。只要对现代社会有具体的了解,只要对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合作体系(比如像俄罗斯这样巨大的国家)有具体的了解,就会立即明白,鉴于现代社会制度被矛盾撕裂,镇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称我们是“国家主义者”,因为我们承认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也因此承认国家暴力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总罢工的实质是使政府机构瘫痪,因此,在政治总罢工造成的情况下,早已过时的、罢工直接反对的那旧政府的暴力已经证明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即使采用唯一能用的野蛮手段也不可能持续控制公共秩序。同时,罢工已使千千万万的工人从走出工厂,冲上街头,已唤醒他们投身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谁能领导群众,谁能使群众队伍遵守纪律?旧政权的哪一个机关?警察吗?宪兵吗?我找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除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谁也不能!指挥这支巨大的自发力量的苏维埃,承担着把内部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预防过火的行为并减少斗争中不可避免的牺牲者,使其尽可能地少的直接任务。既然如此,苏维埃在那场创建它的政治罢工中就成为了革命群众的自治机关——一个权力机关。它以其全体的意志来统治部分。它是一个民主的政权,人们自愿服从它。但是,由于苏维埃是绝大多数人的有组织权力,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迫对那些把无政府状态带入其统一队伍的人采取镇压措施。苏维埃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性政权作为旧机器在道德上、政治上和技术上完全破产时的唯一政权,作为“个人不受侵犯”和“公共秩序”这些词在其最佳意义上的唯一保障,它认为自己有权以武力对抗这些人。完全建立在血腥镇压基础上的旧政权之代表,无权对苏维埃的暴力手段提出道德上的愤慨。检察官在这个法庭上代表的历史政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有组织暴力。由苏维埃作为其前身的新政权,是多数人有组织的意志,要求少数人守秩序。在这种区别中,苏维埃以为之生存的革命权利,是一种超越任何法律或道德怀疑的权利。
苏维埃承认自己有权进行镇压。但在什么情况下镇压,以什么程度进行镇压?关于这点,你们已经听过上百人的证词了。在采取镇压之前,苏维埃以话语劝服。这就是它的真正方法,而苏维埃不知疲倦地使用它。通过革命鼓动,言语的武器,苏维埃不断地使一批又一批群众站起来,服从自己的权威。如果它遇到了无产阶级内部无知或堕落的群体进行抵抗,它就会对自己说,用武力使其无害的时候还远得很。正如你们从证人的证词中看到的那样,它还会寻求其他方法。它呼吁工厂行政人员理智,号召他们停工,通过那些同情总罢工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对无知工人施加影响。它向工人派出代表,以把他们从劳作中“带出来”,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武力来威胁工贼。但它使用过武力吗?法官先生们,你们在预审材料中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例子,而且在法庭调查期间,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也没能成功把它们找出来。即使我们认真对待那些在法庭上出现过的“暴力”例子,它们也都是喜剧性的,而不是悲剧性的,(比如,某某人进入了别人的公寓里而没有摘下帽子,又比如某某人在双方同意下逮捕了某某人……)我们只要把某人忘记摘下的帽子,和旧政权经常错误“摘下”的上百颗头颅相比,工人代表苏维埃暴力的真实面目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而我们不曾是别的样子,也不需要成为别的样子。我们有责任以真实面貌重建当时的事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这些被告都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的审判。
让我提出另一个对本庭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行动和声明是否具有法律基础,是否多少以十月十七(30)日宣言为基础?苏维埃关于立宪会议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十月宣言又是何种态度?我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当时根本没在意过这个问题,但它现在无疑对这个法庭具有很大的意义。法官先生们,我们在这里已经听过了证人卢奇宁(Лучинин)的证言。我个人认为,他的证词非常有意思,而且其中有一些一针见血的深刻结论。他提到,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其口号、原则及政治理念方面是共和制的,实际上直接、具体地落实了沙皇专制在十月十七号宣言原则上宣布的那些自由,而那些把它带到世上的人却实际上反对这些自由。是的,各位法官,各等级的代表!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实际上实施并落实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十月罢工的压力下被许诺给俄国人民的东西。与此相反的是,旧政权的机器只能通过把人民的这些合法成果撕成碎片来回光返照。法官先生们,这些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能就此争议,因为它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或者问我的同志们,我们是否主观地依靠了十月十七日宣言,那么我们将明确的回答“不”。为什么?因为我们深信(而且我们没有错),十月十七日宣言没有创造任何法律基础,没有给任何新法律提供基础,因为我们深信,法官先生们,新的法律制度不是宣言创造出来的,而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真正改组的产物。我们因为采用了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唯一正确的观点,所以认为自己有权利对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内在力量不抱任何信心。我们公开声明过这点。但我不认为,我们作为党的人(Люди партий),作为革命者的主观态度可以使法庭决定我们身为国家公民对宣言的客观态度,决定我们对现存国家体制的成型基础的态度。因为法庭,只要它还是法庭,就必须把宣言看作是自己的法律基础,否则它就必须停止存在。我们知道,在意大利,存在着一个在国家君主立宪的基础上运作的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党。就其性质而言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在所有文明国家都合法且进行着斗争,而它们就自身存在而言也是主张共和体制的。扪心自问一下:十月十七日宣言是否容纳了我们俄国社会主义—共和主义者?这个问题是法庭必须作出决定的。法院必须说明,当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立宪宣言只是一份永远不会被自愿兑现的赤裸裸的承诺清单时,是正确的吗?在对这些书面保证进行革命式的批评时,是正确的吗?在呼吁人民为完全的、真正的自由进行公开的斗争时,是正确的吗?还是说,我们不正确?那么就请法院告诉我们,十月十七日宣言提供的是实际的法律基础,而在这个法律基础上,我们共和主义者是合法有权利的;尽管我们有自己的观念和意见,也是“合法地”行动的。现在就让十月十七日宣言通过法庭的裁决对我们宣布:“你们总是否认我的现实性,可是我对你们、对全国来说都是存在的。”
我已经说过,工人代表苏维埃从未在自己的会议上提出过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问题;然而,正如你们在工人证人的讲话中得知的那样,它对这些口号的态度是明确的。是的,还能怎么样呢?苏维埃本来也不是在空地上出现的。它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经历了1月9(22)日事件的,通过枢密官施德洛夫斯基的委员会,经历了漫长的整个俄国专制学校之后出现的。早在苏维埃存在之前,对制宪会议的要求、对普遍选举权的要求、对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就已经连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成为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核心口号。这就是为什么苏维埃从来就没有机会把这些问题作为原则问题提出来:它只是把这些问题作为一向存在的决定融入自己的决议中了。起义思想的实质也是如此。
起义是什么,法官先生们?不是宫廷政变,不是军事阴谋,而是工人群众的暴动[2]!本庭庭长向一位证人提出了以下问题:他是否认为政治罢工是一种起义?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的了,但我相信并肯定,政治罢工——尽管代表先生们可能有疑问,——实质上就是一种起义。这不是一个悖论!尽管从起诉书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个悖论。我重复一遍:我对起义的概念,(我将在下面证明这一点)与警方和检方构建的这个词的含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说,政治罢工是一种起义。的确,什么是政治总罢工呢?它与经济罢工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都会停止工作。在其他方面,两者并不相像。经济罢工有一个明确的狭隘目标,即通过使个别企业主暂时脱离竞争行列来对其意志施加影响。它中断工厂的工作,是为了在该工厂的范围内实现某些变化。政治罢工在性质上与此有者深远的区别。它不会对个别企业主施加压力,通常不提出任何具体的经济要求;它的要求越过自己大力打击的那雇主和消费者的头顶,针对国家政权。那么,政治罢工是如何影响政权的呢?它瘫痪了政权的生命机能。一个现代国家,即使如俄罗斯一般落后,也依赖于中心化的经济有机体。这种有机体以铁路作骨架,以电报作神经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就算电报、铁路和所有其他现代技术成就不会服务于俄国专制主义的经济或文化目的,这些东西也会对它的镇压活动更加重要。为了把部队从国家的一端送到另一端,为了统一并指挥行政机关针对动乱的斗争,铁路和电报是不可替代的工具。那么政治罢工做了什么?它瘫痪了国家的经济机器,破坏了行政机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孤立政府,并使其无力化。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把工厂和车间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并以这工人大军与国家政权对抗。法官先生们,起义的本质在此。把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一个单独的革命抗议活动中,进而使其与国家政权对立,就像敌人对敌人那样——法官先生们,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理解的“暴动”,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自发地爆发的十月罢工中,我们看到了两个敌对方之间的此类革命冲突。十月罢工发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之前,本身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罢工造成了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一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就是十月十七日宣言。我希望检方不要否认这一点,就像最保守的政治家和政论家,包括半官方的《新时代报》都没有否认这一点一样。《新时代报》是很渴望把革命产生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和一系列其他同类或反面的宣言一起画上大叉的。就在几天前,《新时代报》写道,十月十七日宣言是政治罢工给政府制造的恐慌的结果。但是,如果说这个宣言是整个现行制度的基础,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法官先生们,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是建立在恐慌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恐慌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罢工。因此,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总罢工不仅仅是停止工作那么简单。

(杂工谢利韦斯特罗夫,苏维埃案件的被告之一)
我说过,政治罢工一旦不再是示威的时候,实质上就变成了起义;更确切地说:它成为了无产阶级起义的主要、最普遍的方法。主要,但不是全部。政治罢工的方法有着自己的天然局限。这点,在工人们听从苏维埃号召于10月21日(11月3日)中午12点复工的时候,就变得很明显了。
十月十七日宣言遇到了不信任票;群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政府将无法落实承诺过的自由。无产阶级看到了决定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并本能地转向苏维埃,作为其革命力量的中心。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在从恐慌中恢复过来后,开始重建其半毁的机器,整顿其军团。结果就是,在十月冲突后,出现了两个政权:新的、人民的、以群众为基础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政权,和旧的、官方的、以军队为基础的政权。这两种力量不可能并存:一种力量的巩固就会使另一个有灭亡的危险。
依赖其刺刀的专制,自然要给以苏维埃为中心的人民力量的巨大团结过程带来最大的动乱、混沌和解体。另一方面,苏维埃是建立在工人群众的信任、纪律、积极和一致的基础上的,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政权的军队和所有物质武器仍然掌握在那到10月17日为止沾满鲜血的手中,给人民的自由、公民的权利和个人不受侵犯带来了怎样可怕的威胁。于是,这两个权力机关之间开始了争夺对军队的影响力的艰巨之战——这是日益壮大的人民起义的第二个阶段。在无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大罢工基础上,出现了争取军队到自己一侧的强烈意图,与士兵交兄弟,抓住他们的心。从这一意图中自然会出现对士兵的革命呼吁,因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他们身上的。11月的第二次罢工使工厂和军营之间团结的有力并辉煌的展示。当然,假设军队已经站到了人民一边,就不会需要起义了。但是,我们会认为军队会和平地转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吗?不,我们不这么认为!专制不会坐视军队摆脱自己那腐朽的影响,成为人民的朋友。在失去一切之前,专制将主动发起进攻。彼得堡的工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意识到了。无产阶级、苏维埃相信两个政权的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相信,对此毫不怀疑,知道,清楚地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刻迟早会到来……
当然,假如社会力量的组织过程没有被反革命的任何武装攻击打断,它就会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下继续沿着它已经进入的道路前进,而旧制度则会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被消灭。因为,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工人是如何团结在苏维埃周围,看到了不断吸收农民群众的农民联盟是如何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看到了铁路和邮政—电报工会是如何与苏维埃团结起来的;我们看到了自由职业者的组织工会联盟是如何被吸引到苏维埃身边的;我们看到了工厂管理人员对苏维埃抱的态度有多么宽容、多么近乎友善的。仿佛整个民族都在作出英勇的努力,试图从自己的深处产生政权机关,以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为新制度创造真正的、不可置疑的基础。如果旧的国家政权没有干预这种有机的努力,如果它没有把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带入国民生活,如果这种组织力量的过程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结果就会是一个新的、重生的俄国,非暴力,不流血。
但问题是,我们从来也没有一刻相信解放进程会如此一帆风顺。我们太了解什么是旧政权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尽管宣言看起来像是要与过去进行决裂,但旧的政府机器不会自愿退出,不会把政权交给人民,也不会交出它的任何一个重要阵地;我们预见到并公开地警告了人民:专制主义会做出更多忙乱的尝试,仍然紧握权力不松手,甚至重新获得那些它已经庄严地放弃了的东西。法官先生们,这就是为什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起义——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在人民反对军事警察秩序的斗争过程中,它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历史的必然。在10月和11月,这一思想在所有的会议与集会中占主导地位,支配者所有的革命报刊,注满了整个政治气氛,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在代表苏维埃的每个成员意识中结晶;这就是为什么它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苏维埃决议的一部分,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需要讨论它。
我们从十月罢工继承的紧张形势如下:一个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群众革命组织,不是建立在那不存在的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确实存在的力量上。而武装起来的反革命等待复仇时机。如果可以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这种形势就是起义的代数公式。新的事件只是把新的数值代入了这个代数公式。与检查官作出的肤浅结论相反,武装起义的思想不仅仅能够在11月27日(也就是在我们逮捕的一周前)的苏维埃决定中找到清楚而又明晰的表达,还能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活动初期的决议中,在那些取消葬礼性示威的决议中,在后来宣布结束十一月罢工的决议中,在其他许多谈到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决定中,在谈到最后的攻击或者说是最后的战斗是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时刻的决定中,都可以找到——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本质上一样的武装起义思想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所有决定。
但是苏维埃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这些决定的?它是否认为,武装起义是一项可以在地下准备,然后以现成的面貌被带到大街上的事业?它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起义行为?执行委员会是否发展出了一种街头斗争的技术?
当然不!而这不得不让起诉书的作者走进死胡同。当他面对着为数不多的数十把左轮手枪时,他陷入了迷惑不解,在他眼中,这些手枪是武装起义的唯一真正舞台道具。但他的观点只是刑法的观点,而刑法知道阴谋团体,却无法理解群众组织的观念;刑法知道图谋与叛乱,却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革命。
这一审判依据的法律概念比革命运动的演化落后了几十年。现代俄国工人运动与刑法典解释的阴谋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个刑法典,自生活在烧炭党时代的斯佩兰斯基[3]起就没有变过。这就是为什么,试图把苏维埃的行动放到100和101条的狭隘框架从法律逻辑上看是完全无望的。
尽管如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尽管如此,我们确实在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法官先生,群众的起义是制造不出来的,而是自发的。它是社会关系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在纸上策划的产物。群众起义不能制造,只可预见。由于种种原因,公开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那些原因既不取决于我们,也不取决于沙皇制度。公开冲突一天一天在迫近。对我们来说,准备公开冲突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把这场冲突的牺牲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是否认为,为了这个目的,首先需要储备武器,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为起义的参加者规划位置,把城市氛围若干个区——换句话说,做所有的军事当局在预估“混乱”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把彼得堡分为若干个区,为每个区分配一个上校,然后给他们配备一定数量的机枪、弹药和人?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作用的。为不可避免的起义做准备……法官先生,而我们,不曾像检方想的和表达的那样准备过起义,我们使自己对起义有准备——这点对我们来说,首先就是要启发人民意识,向他们解释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给予他们的一切都将再次被夺走,只有武力才能捍卫权利;工人群众的强大组织是必要的;必须挺起胸膛直面敌人,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没有别的路可走。这就是我们说的“对起义有准备”。
我们认为,在什么条件下,起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呢?军队的同情!最首要的,就是必须把军队拉到我们一边。要迫使士兵认识到自己正在扮演的可耻角色,说服他们与友好的人民合作,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我已经说过,十一月罢工是对受到死刑威胁的水兵直接的、兄弟般的同情产生的无私冲动,同样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它把军队的同情心和注意力引向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检察官本该首先在那里调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但是,展示同情和进行抗议当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那时和现在认为,是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期待军队站到革命的一侧?为此需要些什么?机枪和步枪?当然,工人群众如果有了机关枪和步枪,那么就掌握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起义的不可避免性。摇摆的军队会在武装起来的人民脚边放下武器。但是群众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拥有大量的武器。这是否意味着群众注定要失败?不!不管武器多么重要,法官先生们,主要的力量不在于武器。不,不在于武器!不是群众有杀人的能耐,而是他们有准备赴死的伟大决心——瞧吧,法官先生们,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正是这,保证人民起义最终胜利。
当被派到大街上镇压人群的士兵与其面对面,并发现这人群,这人民在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以前不会离开时,发现这人群准备好面对成山的尸体时;当他们看到并确信人民认真地投入战斗,并战斗到最后一刻时,士兵的心,就会像在所有革命中出现过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动摇,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怀疑他们服务的秩序的坚固性,不得不相信人民会得到胜利。
人们习惯于把起义与街垒联系起来。即使抛开街垒在起义中过于有代表性这点不谈,我们也不应当忘记,街垒看上去是起义的纯粹机械因素,却首先发挥的是道德上的作用。因为在所有革命中,街垒并不起堡垒在正规战争中起物理障碍的作用——街垒是为起义服务的,通过为军队的调动制造临时障碍,使其与人民密切接触。在这里,在街垒边,士兵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诚挚勇敢的话语,兄弟般的呼吁,人民良知的呼声——士兵与公民在革命热情气氛中这样接触,其结果就是旧军队纪律的绳索突然绷断、溶解、消失。正是且只有这一点,保证了人民起义的胜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人民起义并不是在他们被机枪和步枪武装之时准备好(因为以这一点来算,它永远也不会准备好),而是在它准备好在公开的巷战中死去之时准备好。
但是,旧政权当然看到了这种伟大感情的增长,这种为祖国利益的名义牺牲的能力,为后代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生命;看到了群众被这种与它格格不入的、它不熟知的、与它敌对的热情感染,这一被包围的政权无法让自己静静地看着人民的道德重生在自己眼前完成。对沙皇政府来说,被动地等待,就意味着注定使自身不复存在。这点是清晰的。那么它能够做什么呢?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和一切手段来与人民的政治自决做斗争。无知的军队和黑色百人团,警探和卖身投靠的报刊对此同样适用。唆使人们彼此对立,在街道洒满鲜血,抢劫、强奸、纵火、制造恐慌、撒谎、欺骗、诽谤……这就是旧的、罪恶的旧政权能够做的事情。它做了所有的事情,而且直到今天也还在做这些事情。如果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肯定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死敌力图使其更快到来。
你们在这里已经多次听到,工人在10月和11月武装起来反对黑色百人团。如果人们对这个法庭外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就会无法理解,在一个革命国家里,在一个绝大多数居民都支持解放理念的国家里,在一个人民群众公开表示做好准备战斗到底的国家里,几十万工人为什么会武装自己,与弱小到只占人口微不足道部分的黑色百人团作斗争。难道这些各阶层的社会渣滓、社会败类真的有那么危险吗?当然不是!如果只有黑色百人团这样可怜的匪帮挡在了人民的道路上,那任务可就简单多了。但是,我们不仅从证人布拉姆松律师那里,而且也从上百名工人证人那里听到了大量的证词,说明黑色百人团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支持——如果不是全部支持,也是它很大的一部分支持;说明在那些一无所有、不留活口——不留白发老人、不留无力自卫的妇女、不留孩子的流氓匪帮背后,站着的是政府的特务,他们无疑是用国家预算的资金来组织和武装黑色百人团的。
最后,难道我们在本次庭审之前,不知道这些吗?难道我们不曾读过报纸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过目击者的报告,没有收过信,没有亲眼看到过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乌鲁索夫亲王那令人震惊的披露吗?检方对这一切并不相信,因为他不能相信。否则,他就必须转而去控告他现在保护的那些人,而且必须承认,俄国公民用左轮手枪武装自己反抗警察是自卫行动。但法庭相信当局的屠杀活动还是不相信,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对这个法庭来说,只要我们相信这点,在我们的号召下武装起来的数十万工人对此深信不疑,就足够了。我们毫不怀疑:流氓匪帮的门面背后是统治集团的强有力的拳头。法官先生,就是此刻,我们也能看见这双邪恶的拳头。
法官先生,检察当局要你们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武装工人是直接地为反对现存“政体”而进行斗争。如果明确问我:“是这样的吗?”我会回答说:“是的!”是的,我承认这一指控。但只有一个条件,我不知道检方和法庭是否同意这个条件。
我倒要请教:检方所说的“政体”确切涵义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当真都在某种政体下生活吗?这个政府早已用自己的军事—警察—黑色百人团机器和全国人民决裂了。我们身边的,不是国民的政权,而是一架进行大屠杀的自动机器。对这架把我们国家肉体活生生地剁成碎块的政府机器,我找不出任何别的名称来形容。要是你们告诉我杀人、放火、强奸……,要是你们告诉我在特维尔、罗斯托夫、库尔斯克、谢德尔策……发生的一切,要是你们告诉我基什涅夫、敖德萨、比亚威斯托克是俄罗斯帝国政体的代表,那么——是的,那么我就同检方一起承认:我们在10月和11月里是在直接武装自己,来反对这个俄罗斯帝国的政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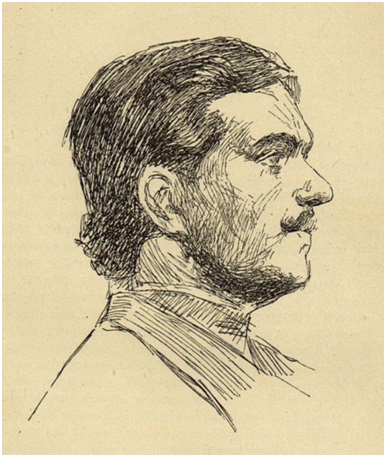
(工人菲利波夫,其中一名被告)
[1] 译者部分参考了伊萨克·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王国龙译,施用勤校)的译文。——中译者注
[2] 起义和暴动在俄语里可以是同一个词。——中译者注
[3]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伯爵(Граф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перанский,1772年1月12日—1839年2月23日),俄国政治改革家。出身于牧师家庭。1795年起进入俄罗斯帝国内务部工作。1797年进入总检察长办公厅工作。1799年起任国务委员。1808—1809年任司法部副大臣。1809—1811年任芬兰事务委员会国务卿。1810年加入共济会。1810—1812年任国务院国务秘书。1812年被解职并被流放到彼尔姆。1814年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1816—1819年任奔萨总督。1819—1821年任西伯利亚总督。1821—1825年任国务院法律司委员。1825年参与审判十二月党人,持同情态度。1826—1833年期间参与编纂《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1835—1837年担任亚历山大皇太子(即亚历山大二世)的法律和政治学教师。1838—1839年任国务院法律司司长。1839年被封为伯爵,同年2月23日去世。——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